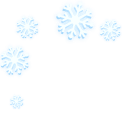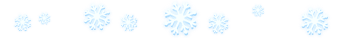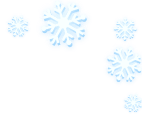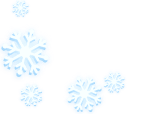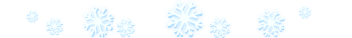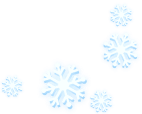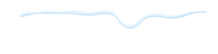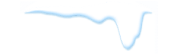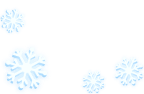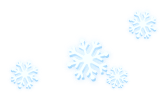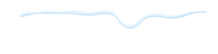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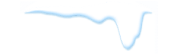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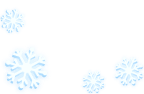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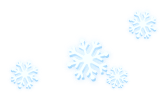
当喜悦成为习惯
安详本身就是喜悦。
就像月光,无论照在谁家的屋顶上,它的清辉都是皎洁的。
就像清泉,无论用什么勺子舀出来,用什么杯子去喝,它的味道都是甘醇的。
孔子六十而耳顺,说明孔子六十岁时已经被喜悦充满心田,而且是无条件地充满,环境已经无法影响这种喜悦,任何恶风苦雨已经无法影响这种喜悦。
庄子能够在爱妻去世时鼓盆而歌,说明他的喜悦已经超越了生死,或者说,就连生死都无法在他的喜悦之海中激起一丝涟漪。
佛陀可以坦然地接受婆罗门吐在脸上的口水,说明他的喜悦已经盛大到可以把一口口水忽略不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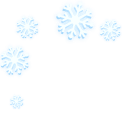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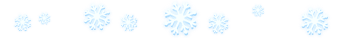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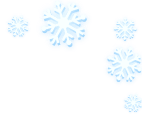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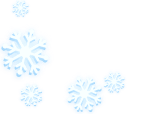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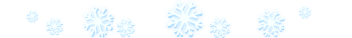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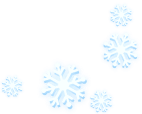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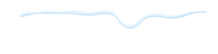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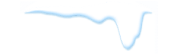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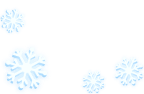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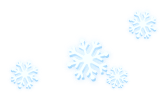
相传大学士苏轼被贬到江北瓜州时,和仅一江之隔的金山寺住持佛印交情甚笃,两人经常在一起高谈阔论。
一日,他自觉修持有得,即撰诗一首:“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再三吟咏,颇为自得,便派书童过江,送给佛印印证。
岂料佛印阅毕,只是莞尔一笑,不疾不徐地批了两个字,随即交给书童原封带回。
欣然等待佳音的东坡居士,以为禅师定会赞叹一番,急忙开封。
万万没有料到,诗稿上面被歪歪斜斜地批了“放屁”两个大字。东坡非常愤怒:“岂有此理!本居士一定要讨个公道。”随即叫书童备船渡江。
船刚靠岸,便发现佛印身边的一位小和尚已经含笑相迎了。小和尚说,他家师父今天行脚在外,让他把这封信转给大居士。
东坡展信一看,就傻了眼。
只见信上写着:“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
东坡恍然大悟,面红耳赤,惭愧不已。
夸口“八风吹不动”,竟然“一屁过江来”,东坡与佛印的修持,孰高孰下,不言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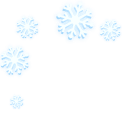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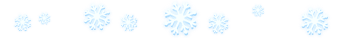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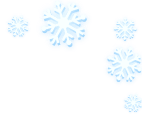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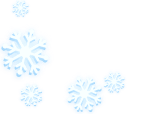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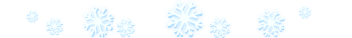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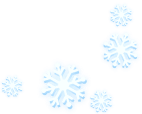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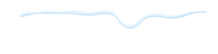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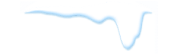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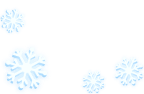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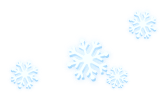
看完这个故事,许多人都会取笑东坡居士,却很少有人取笑自己。
细究起来,我们可能天天都在“过江”呢,弄不好我们可能一天要“过”无数次“江”呢。
那是因为我们的心里有太多的风,有远比东坡居士多得多的风。
识破“八风”(利、衰、毁、誉、称、讥、苦、乐),是收获喜悦的关键。
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成人所不能成。
当喜悦成为习惯,这个“忍”都没必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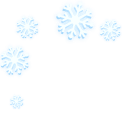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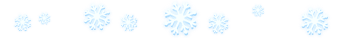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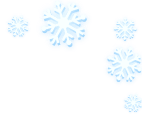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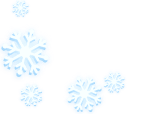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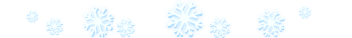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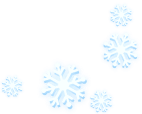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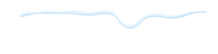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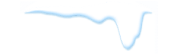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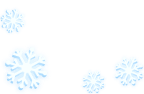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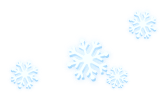
当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处在喜悦中,那么他就是真正的富翁、真正的王、真正的仙了。
还求什么?
对于生命来说,喜悦难道不是它全部的意义吗?
那么,不管从事什么,不管身在何地,只要我们在收获喜悦,不就在最大的实现中吗?
请问,除过喜悦,我们还要实现什么?
我们追求财富,不就是追求财富带来的喜悦吗?
我们追求权力,不就是追求权力带来的喜悦吗?
我们追求爱情,不就是追求爱情带来的喜悦吗?
我们追求荣誉,不就是追求荣誉带来的喜悦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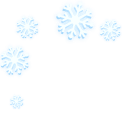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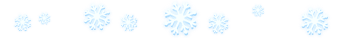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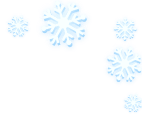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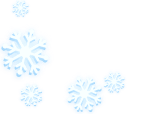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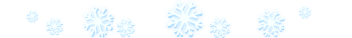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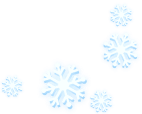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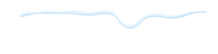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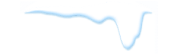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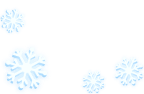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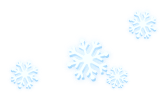
可是,如果我们在当下就能让喜悦充满,我们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
我们追求的,不就是这个“满”吗?
如果我们在当下就能把喜悦的坛坛罐罐装得满满当当的,还需要起早贪黑地去千里之外挑桶水回来吗?
现在,我们已经沉浸在喜悦的大海里,我们还需要不辞辛苦地去江河里再挑一担水来沐浴吗?
可是,现代人不就在乐此不疲地干着身在大海还觅江河的事吗?
生命因为太多的多此一举而憔悴不堪,而疲于奔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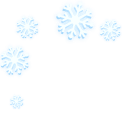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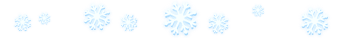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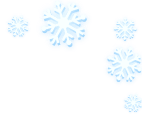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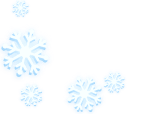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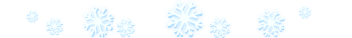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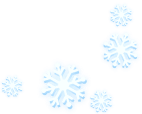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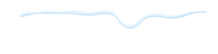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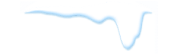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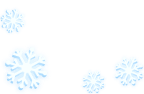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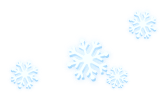
奔命,成了现代人的生动写照。
因为这个“奔”,我们和大地错过,和岁月错过,和时间错过,和喜悦错过,最终和生命错过。
生命成了一个大大的亏损。
不管我们绘制多么宏伟的蓝图,从事多么伟大的事业,如果属于喜悦的账面上有出无进,那么我们肯定在和生命错过。
我们的两眼应该紧紧盯着喜悦开盘,这样的股才是“牛股”,这样的市才是“牛市”,否则,等待我们的肯定是“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