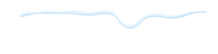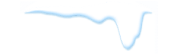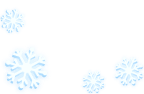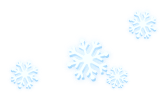十三个大包子
作者:凌迅
本篇文章选自《“老五届”三十年风云录》其二《酸甜苦辣自己说》
1970年8月,我作为69届毕业生与70届毕业生一起到某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在军垦农场十六个月里,平生唯一一次吃过十三个大包子,使我终生难忘。
我们所在的那个农场,原先农忙时由所属部队的战士连队去耕种,去收割,闲时则只有留守人员,所以虽是顶着一个连的建制,却只有指导员、连长及另外的两名副职;至于炊事班,则仅班长一人,炊事员一人,司务长一人而已。突然接到命令要接纳一百多名大学生来农场接受“再教育”,你来我往,人影幢幢,顿时使昔日冷清的营房热气腾腾起来。这可就忙坏了炊事班,人手不够,除实行副班长轮流值日,以贯彻民主管理制度外,碰上节假日或者改善生活的时刻,不得不动员能做饭的人去做力所能及的活。
我们到达农场的时候,小麦早就收割完了,在大片田地里,高处种着黄豆,低洼处种着红麻。三百多亩土地,原先只有那么几个留守人员照看,“草盛豆苗稀”,势所必然。也许早就考虑到 了收获的时候会有许多人来吃饭,在一块较大的土地上,种上了不需多少照管的茄子;此外,还有几架西红柿,也只是任凭其疯长。人来得太突然,又来得太多,没有别的蔬菜可吃,又不能不给菜吃,没有别的办法,就只能是中午煮茄子,下午西红柿汤;或者中午西红柿汤,下午煮茄子。一开始大家还能接受,因为似我们69届毕业生,已经在学校多困了一年——“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许多部门、许多机关都因两派斗争中止了正常工作,即使工军宣队进驻,也只是领着“深挖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路线”,哪有心思去研究职能工作呢!更何况办学习班,上五七干校,许多机关的人都朝下赶,根本提不到进人。举目四望,纷纷纭纭,茫然无绪,我们不能不为我们的人生顿感悲凉、烦闷——现在能到军垦农场来,有一个中间环节,也许会等得光明到来,心里不由滋生这总比困在学校无所事事要好得多的思想。 另外,也因为能吃饱饭。我们1964年入校的时候,由于三年经济恢复已见成效,饭桌上总布着四菜一汤,使我们来自农村的学生大饱眼福,大享口福:从来没吃过的米粉肉第一次尝到了,从来没见过的熏鱼第一次见到了,从来没吃过的海米鸡蛋白菜第一次吃到了……真是过年一样,简直就是日日过年。“文化大革命”风暴卷起,不时伴有枪炮轰鸣,就使学生的供应难以为继:油菜蛋肉的来源是农村,“文化大革命”中要“革命”的一定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只能捆在田地里,不准多养猪,不准多养鸡,不准多种菜,还硬性规定不准进自由市场,只能自种自吃,自养自食;种地只许种高产作物,低产的油料作物被限制得很死很死,农民自身就没有油吃,纵然实行统购统销,事实上根本没什么可购,自然也难以实行什么统销了。初入学时的丰盛菜肴不见了,学校的食堂师傅被推拥为工人阶级,忙着去占领上层建筑;管理人员大多靠边站,食堂到时候能开伙就不错。我们只能每天点一遍饭菜票,计划每天花多少饭票,花多少菜票,然后拥挤着冲进食堂,能买上饭菜就心满意足。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年,好容易混到了离开学校,到农场能吃上茄子,能喝上西红柿汤,而饭则敞开吃,便大有脱离苦海的感觉。
不过,要我们到军垦农场来,决不是因为西红柿汤、煮茄子没人吃——连队很快便对我们实施“再教育”的计划了。一开始的劳动是薅草施肥之类,还难不倒也累不着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学生。难过的关口一是军事训练,二是“斗私批修”。我们一到军垦农场,就脱下了学生服,换上军装。所谓军装,是在提倡艰苦朴素的年代,又处于艰苦的岁月中,被解放军战士洗了又洗,补了又补的旧军装。实在不能再洗了,实在不能再补了,就作退役处理,准备用来擦炮。来部队的大学生只是接受“再教育”,并未纳入军事编制,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就只好 启用这些本该报废的物资。这些旧军装白不白绿不绿,补丁摞补丁,一件足有七八斤重,穿在身上好似古战场捡回来的破旧盔甲。穿着这样的旧军装,不是军人,又像军人,然而绝不是正规军人。当地老乡怎么也看不顺眼,想不出这是从哪里招募来的苦力;而从城市来探亲的故旧情侣,乍入目还以为是劳改农场的劳改犯人。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凡具有一定知识的人,就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只是大小有所区别罢了。而知识分子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在资产阶级还存在的条件下,始终被视为一种游离因素,多数都被冠以“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头衔。虽然,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是随着共和国成立成长起来的,共和国曾寄予我们厚望,说什么“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虽然,我们“根红苗壮”,经过了一道道政治审查,多数是被做为“绝密人材”招考进大学的;只是因为上了大学,而学校被所谓资产阶级“把持”,就狐疑我们这些“毛”没有长到无产阶级那张“皮”上,因而最有可能被资产阶级所争取,成为复辟的社会基础。天安门广场的接见,热泪满面,高呼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你斗我卫,都是集中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下,却不能洗去对我们内心的不信任感,认定只有让我们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才有可能走到革命队伍中来。我们自知悬在头上的这把剑是何等锋利,便毫无难色地穿上破旧的军装,做起通过劳动实践改造自己的“犯人”来了。
松散惯了,不论怎么情愿,只要穿上破旧军装,都感觉是一种严厉的约束,觉得从四面八方投射过来的审视、挑剔的眼光,使我们不能不时时处处扣好风纪扣,挺着胸膛。不仅如此,站队,集合,摸爬滚打以及夜间的紧急集合,也完全军事化,完全正规化。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铸造成一个兵,实现与工农兵的紧密结合。比如紧急集合。也许我们还年青,尽管疲劳连着疲劳,就在我们一上床就能酣睡的那一刻,当尖厉的哨声划过营房的夜空时,我们还是霍然而起,跃然穿上裤子,找着鞋子,打好背包,很短的时间就能站在门口,等齐了由班长带着跑步进入操场。然后根据假设的敌情,跑步前进,朝目标围绕过去。自然洋相多有,穿反了鞋子的,穿错了裤腿的,背包半途中散开,只能裹挟着前进的……诸如此类,均属挨批的对象。比我们年龄还小的年轻排长,言辞却很老辣,板着脸训斥着,甚至咬着牙根痛骂我们。那些言辞像似一条鞭子,不住地抽打着我们的自尊。这时,尽管挺着脖子,心里却是蔫蔫的,久了也便麻木了。
在那个时候,对大学生实行“再教育”的最主要内容及最主要的形式是“斗私批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内容纵然多多,“斗私批修”可谓最富有创造色彩。因为“斗私”与“批修”,把主观与客观、内心与外界、个人与时代、国内与国际几个方面都统一了起来。于是言无大小之别。无巨细之分,一置于“斗私批修”的范围,就“事事联着纲和线”、“休戚与共五大洲”。本来,我们从农村走来,到城市读书不过六年的时间,从来没有到过“修正主义”所在的地方,不知道修正主义为何物;本来,我们从城市被抛向偏僻的海隅,于社会于时代几乎割断了联系,不知修正主义怎样袭来,却硬把我们置于宙斯的殿堂上,这本身就很荒谬,因此所谓“斗私批修”就很空泛,几乎近于无聊。但迫于无奈,我们在形式上又不能不很严肃的进行下去。这种场合,往往大多作苦思冥想状,作肃穆庄严状。为了应付这种气氛,或者不如说要驱走这种气氛,男生都学会了抽烟。由于没有多少钱买烟,就请家里寄来烟叶,晒干,碾碎,用纸卷成大喇叭,一支能装进半两烟末,然后点着就喷云吐雾起来。十几支烟枪齐举,“斗私批修”的气氛便顿时“深沉”起来,“火药味”也顿时十足起来。当然也不尽为空谈,也有非常具体的事例,就是每天的累,每天的苦,每天面对的煮茄子或者西红柿汤,这些是拂之不去的现实,而且是想脱离都脱离不掉的现实。我们又没有修炼到“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程度,难免会有不悦之色,不满之意。这不论是自己察觉到的,还是被别人捕捉到的,都构成了“斗私批修”最生动的话题。当然,这些问题太普遍了,“上纲上线”也不能开除球籍,往往就在“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的鼓动声中偃息下来。
由于我们连队所处的地理形势高不高、洼不洼,不能种植水稻,只能种红麻。别看我们初来时,红麻苗像秃子头上的头发斑斑落落,待薅去了杂草,施上了化肥,红麻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快速地长起来,有的麻杆竟能长到像拳头一样粗,远远望去,犹如南方竹林般高耸茂密,十分壮观。红麻是一种经济作物,主要用来编织麻袋,在我们的化纤工业还没有上马的情况下,当时绝对是供不应求。这是农场的一笔相当重要的收入,因此就收获而言,农场领导是相当重视的。我们每个人发一把胶东人用来砍山草的大镰刀,站在田头,向红麻宣战。红麻的叶很粗糙,打到身上,就会划出道道血痕。好在我们穿的旧军装补了一层又一层,倒成了良好的护身盔甲。红麻长得太粗了,一镰刀下去硬是砍不断,镰刀用不上几次就会卷起刃来,不得不经常蹲下来在磨刀石上磨。一天下来,腰酸,背疼,脖子软,连手都僵硬得合不拢。
红麻撂倒之后,就平放到地里,任凭风吹日晒,把它们晒干。这中间,得不断地翻晒。这时的田地失去了红麻的遮蔽,一望无际,只有衰草瑟瑟,孤雁哀鸣。如果风稍微一大,枯叶随风卷起,一片苍茫,一片空旷。身着旧军装的我们,踽踽行进在红麻地里翻晒红麻,几乎与天地混为一体。“斗私批修”的结果,已经把三线的话都掏出来了,并信誓旦旦地表示不敢再蹈覆辙,几乎同草木一样无知无觉,任凭时光老人的荣枯、虐杀与滋生。待红麻晒干之后,就要搬回指定的地点。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即使有,田埂蹊径也进不来。按照实际情形,按照惯例,只有靠人用肩把它们扛出来。我们把红麻一个个交叉起来,在交叉的结合部用尚未干硬的红麻把它们扎牢,由自己或别人发上肩背,扛起来就走。身体强壮的能扛到十三个(捆)或者十五个(捆),身体弱的同学最少也能扛到五个(捆)。肩扛红麻就像肩起一座小山,大家相间相续,来来回目行走在洼地上,好像连绵不断的山脉在移动,在起伏。红麻收获完毕,便真正步入农场的农闲期了。当然也会生出许多新的谋划,比如疏通水渠,以备来年灌溉。在实施“再教育”的人看来,人之所以修,之所以变,就在于脱离生产实践,就在于脱离劳动大众,所以,绝不可让接受“再教育”的人有一刻脱离生产实践。可是我们这些人毕竟来农场很长时间了,也该有个休整调养的机会了。这时,我们种的大白菜已经到了冬储的时刻,栏里养的猪也已长到成色,于是,连里就决定吃一顿大包子。这个消息一传出,整个营房就像盼到了胜利一样,不管帮过厨的还是没有帮过厨的,都走向了厨房。那天是我当值班班长。我同来帮厨的同学们,把大白菜一筐筐的运来,掰去老帮,在清水里清洗之后,就送上菜案子。厨房里刀不够用,就到随军家属那里借。一时间,不知有多少刀在案子上翻飞,剁菜声能传出三五里地。猪由有经验的班长去杀,去毛,开膛,掏去杂秽,几个人齐呼拉把两扇猪肉提向大案子。菜馅好了,肉馅也好了,面也发起来了,整个厨房里站满了包大包子的人。相比较而言,还是吃的人多包的人少,而且包的人都知道这顿大包子每个人定不会少吃,于是举起大手,抓一大团面就是一个剂子,擀出来的皮像油饼般大。没有那么多的勺子去装馅,筷子又不济事,不知是谁出了个好主意:用碗。一碗就是一个包子的馅,又快当又利落。厨房里有十三架笼屉,因为做包子,都清洗出来,都用了起来。先上笼的熟的快,就抽出去倒出包子,又装上新包的包子重新上锅。一笼笼的包子,放在篮里,放在面案上,等待晚饭的哨声。各个班早已做好准条,哨声一响,一齐出动,比紧急集合速度还快。不过,包子太大,领饭的盆一盆装不了几个,一人一个就没有了,于是再领。我住的一班宿舍是各班通向厨房的必经之路,我坐在门口瞧着,只见领包子的人一个接一个,一溜小跑,真称得上是“川流不息”。
这一顿大包子,我吃了十三个。我不知道是怎样吃下去的,也不知包子的生熟及口味,只是点数,可以说是在一个接一个的过程中完成的。吃到十三个,不是不想吃,也不是不能吃了,而是另有原因。我还不满十岁的时候,曾跟随祖父陪伴一个大夫去亲戚家看病人。亲戚家住在城里,开着一个茶馆,另外带卖自己煮的红烧肉以帮衬生计,他招待大夫、祖父就是用的红烧肉。大夫、祖父、亲戚在杯酒之间,不时停下来讨论病人的病情。亲戚、祖父的注意力在病情不在饭,大夫也只能随着在病情不在饭。我在其间,看到满桌子的肉,又从来未闻过这肉的种种香味,真是馋涎欲滴。因为我是小孩子,他们不在意地让我吃,自己则忙着咨询与推究,顾不到我。于是,我便不停嘴地吃。不知道吃了多少肉,也不知道吃了多长时间,直到吃不下去了,方才停下来。在回家的路上,我只觉肚子饱胀,想吐都吐不出来,只好挺着肚子慢慢地蹭回家。我母亲见状,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就把吃肉的情形说了。母亲扒开我的裤子一看,肚子像西瓜一样滚圆,上面的筋都一清二楚地凸现着,就擀,就揉,总不济事。我整整撑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拉了一大摊,肚子方才松快了一些。大概这次吃肉给我留下的教训太惨痛了,所以这次我不敢太放量吃。
在我的记忆中,我还亲眼见到别人被撑坏的情形。那是在1960年,饥饿的年代。一个男同学和一个女同学想赌一次,男同学赌是想吃一顿饱饭,女同学赌是想赌回来一个月的饭票,筹码是二十四个窝窝头,不准喝水,不准吃咸菜,一口气吃下去,那时窝窝头全用地瓜面做,不发,黑乎乎的,六个一斤。男同学吃到十六个,春风得意,吃到十八个就难下咽了。可是吃下去的信念不能动摇,一动摇,整个月的供应就要拱手让给他人;又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多同学呐喊助威,这个面子也不能丢。女同学看到这种情形,放宽了条件,允许用水送,允许吃咸菜,男同学这才死撑烂填地把二十四个窝窝头吃进去。男同学虽然赢了,但在事后的半年里,就没有见到他脸上有过血色,总是苍白干黄。后来又听说他在当兵查体的时候,体检大夫怎么也找不到他的胃,找来有经验的大夫相助,才确定他的胃已偏离了正常位置。这个男同学的教训使我认识到:饥饿固然可怕,撑胀同样可怕。鉴于己,鉴于人,我只能适可而止。
不过,包子这么大,能吃到十三个,也很可观了。在一次与班长独处的时候,我怎么也按捺不住心中的隐秘与窃喜,说出我吃了十三个大包子的事来。谁知,班长竟脱口而出:“我吃了十四个!”天啦,竟然还有比我吃得多的人!我们不禁相顾大笑,笑得那样惬意,笑得那样坦然,笑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大笑。我到军垦农场以后,从来没有这样笑过;离开军垦之前,也再没有这样笑过,这是唯一一次在军垦农场的开怀大笑。这一欢笑,抖落掉“斗私批修”给我脸上刻下的严肃,冲刷掉繁重的劳动在我脸上烙下的愁苦,而心中的隐秘郁闷也自然而然宣了。接连几天,只要几个人凑到一起,就会说起这次吃大包子,相互递传着更为惊人的消息:“九班女班长吃了十八个!”“司务长说,这次吃大包子,一个人合一斤二两肉,三两油,将近三斤面!”
离开军垦农场已经二十七八个年头了,步入社会所经历的风风雨雨,自己人生道路上的诸多烦难坎坷,几乎把农场的许多人许多事都挤压得没有位置,却怎么也拂不去这次吃大包子的情形,一想起它嘴角就泛起笑意。儿子问笑什么?妻子说笑什么?我就绘形绘色地讲述一遍。也许那是我在那个时代一次真正的满足,也许那是我年轻时一次最高的补偿,所以经久难忘。尽管那个时期早已终结,而我也已经不再年轻,但是它最终在我们的人生中,在我们的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使我们体会逝去历史的滋味,去认识现实中的诸多烦难,并还将告知我们的后人:我们曾经经过什么,我们曾经满足过什么,以及这种经历和满足是怎样影响了我们人生取向的形成。而这种人生取向,形成了我们特有的价值体系,以致在我们正式登上社会舞台后,影响着所扮演角色的广度及深度。
作者简介:孔令新,笔名凌迅,男,山东曲阜人,1943年3月生,中共党员。196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现为山东文艺出版社编委会副主任、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