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沼泽地
——六朝诗歌
中国诗歌,挥舞起《诗经》、“楚辞”两杆呼啸的长鞭,经《古诗十九首》的辉煌转折,到了南北朝,似乎闯入了一块艰难的沼泽地。
诗歌在泥潭之中翻滚、徘徊,诗人在泥泞之中艰难地跋涉。我们可以开出一个前赴后继的长长的名单:陆机、潘岳、左思、刘琨、郭璞、陶潜、谢灵运、鲍照、江淹、谢眺、沈约、庾信……然而在这个诗人群落中缺乏顶天立地的巨人,也缺乏元气淋漓的佳作。
除了陶渊明的诗自然清新。
陶渊明以其优秀的文学才能、深邃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陶渊明:我用尽了全力,才能过上平凡的一生。
https://mbd.baidu.com/ma/s/3utLMvo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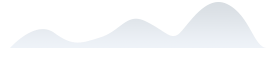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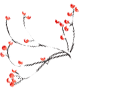
其他大都“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在技法、修辞、声律上费尽了心思,耗费毕生精力,到头来也只是有好句而无好篇。人们对此嗤之以鼻,斥之曰:齐梁绮靡之音。
“梁之冠绝、唐之先鞭”

诗学史家对此倍感困顿:
为什么诗歌到六朝会出现一个低谷?
为什么六朝诗歌杂芜纷陈缺乏一位领袖人物?
为什么六朝诗歌如此地偏重技巧,注意雕饰?
为什么六朝诗歌只能以句摘而不能以篇寻?
他们寻找了所有的社会原因,诸如战乱连年、频繁更替地改朝换代,世风的没落奢侈、诸侯割据下天地的狭小,心态的局促等等,但终觉隔靴搔痒。
艺术只能是艺术,艺术有它内在的意蕴。
记得刘熙载在《艺概》中对诗的艺术境界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认为:诗要经过由“无法”到“有法”,再由“有法”到“无法”的过程,也就是说,诗歌要完成由自然状态到自由状态的飞跃。其间要走过一块艰难的沼泽地。要有诗的自觉,要有对诗的技巧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当技巧成为内在生命的冲动,成为一颦眉、一举手、一投足之间的潇洒和韵味时,诗便达到了自由境界。
六朝是诗歌的自觉阶段,是诗由自然状态向自由状态腾飞所要经历的一次痛苦的裂变。诗不再是无意间的情感构成而是一种殚精竭虑的创作,技巧自然会被抬到显赫的地位。历史注定了六朝诗人只能充当普罗米修斯似的悲剧角色,把技巧熔炼得极为精致,输送到诗的王国,而让唐人占尽风流。
“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刘勰《文心雕龙》),六朝诗人对辞采确实有极大的兴趣。他们自觉地把诗歌语言的审美特质发挥到极致,对诗歌语言的对称、平衡、协调、和谐、错综、统一种种规律作了空前的发掘和通用。这种刻意追求的结晶便是“永明体”,和晋宋以来对偶形式的熔合,它标志着中国近体诗的开端,同时也标志着诗歌格调又跃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永明体
沈约“长于清怨”:
上有离群客,客有慕归心。
何延“平易晓畅”:
野岸平沙合,连山远雾浮。
谢眺“寄情山水”:
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落。
谢眺在这个新的天地里初试锋芒并有所成就。他的“天际识归舟,云中辩江树”,“余霞散成倚,澄江静如练”,都极近唐人风韵,可以说,在六朝诗人辛勤的跋涉中,谢眺已经到了沼泽地的边缘。
六朝,不是诗的误区,而是诗由自然状态走向自由状态所要穿越的黑洞。那种雕章琢句、惨淡经营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诗的自然美,但却是一种必要的修炼。当这种修炼达到炉火纯青、心领神会的程度,当技巧化为血液在生命中涌动的时候,一个鲜活的胚胎便诞生了,那就是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