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的转折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南朝萧统选录的古诗集。
也许人们会普遍认为,在中国古典诗词总汇中,《古诗十九首》只不过是轻飘飘的一页,它过于单薄,难以承担扭转乾坤的任务。
其实,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以数量多寡论,主要是看它是否具有新意,是否对后世文学具有艺术上的启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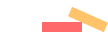
汉代是经学盛行的年代,《诗经》被阉割为儒学道德信条,“楚辞”降格为夸饰帝业的汉赋。
在堂而皇之的皇家气派面前,诗歌似乎找不到它合适的土壤,是有汉乐府民歌悄悄地在民间活跃着,尽管它朴实清新,豪野火辣,但它毕竟带有极大的随意性。
于是,东汉末年诞生的《古诗十九首》就历史性地担负起承前启后的重任,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开一代先声。



从内容上说,《古诗十九首》唤醒了人的生命意识,标志着人的觉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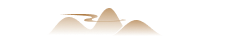
也许是东汉末年的战乱过于频繁,战火硝烟使建功立业成为泡影,儒学信条更显得相对虚伪,生命本体便显得相对重要,人们便掉过头来审视自身,体味到人的渺小、宇宙的浩渺无穷。在人与宇宙的对峙中,人们感到迷惑、恐慌,忧虑,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油然而生,这就是《古诗十九首》的主旋律。这种旋律一直在建安、晋宋的上空迥荡。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古诗十九首》是建安文学、魏晋风度的前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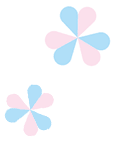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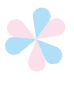
认识自己,战胜自己是人类一个永恒的课题。
《古诗十九首》中那种觉醒的生命意识为诗歌开辟了一个更细腻更富弹性的空间,它把诗人明亮的眸子引向那个大写的“人”字。
从此,诗歌多了一个永远也道不清说不明的话题。在这种难以名状的捉摸中,诗歌拥有了一份朦胧。也许宋词在那段挥不走抹不去的闲愁,可在《古诗十九首》中找到它的生命底色。
与四言相比,五言诗无疑具有绝对的优势。它打破了四言诗的规整和端庄,在那过于严峻的板块里添置了一个活动因子,用奇偶的变化与错位来追求平衡中的不平衡或不平衡之中的平衡。因而,五言诗比四言诗更富于变化,更具有灵性,而且有更强的涵盖力。


让我们还是以事实说话吧。
从《古诗十九首》中随便挑出一句,即如“明月何皎皎”,如果用四言表达则是“明月皎皎”,但“明月皎皎”是对客观物象的静态描绘,“明月何皎皎”却带有浓郁的主观情感,在对月的近似无理的询问中,表现诗人的痴怨。四言诗倘要表达这种情怀,则要添上一句,“明月皎皎,何其然也”,这样一来,便显得松垮和游逸,倘若执意强行把它挤压成四言句式:“月何皎皎”,则又显得有几分生硬和别扭。
因此,四言较五言,虽只字之差,但可谓一字千金。仅这一字的变化,便标志着诗歌史上的一次飞跃。
当然,汉乐府民歌中时常杂有五言甚至至七言,也有如《陌上桑》那样纯用五言的诗歌,但《古诗十九首》将其文人化、规范化;班固的《咏史》史称是第一首文人五言诗,但它“质木无文”,毫无生气,《古诗十九首》将其生动化,成熟化。


《古诗十九首》在诗歌史上虽只短短的一瞬,但它把歌引向对人的思考,对心灵的观照,使诗趋向细腻和迷茫,它完成了诗歌形式由四言向五言的飞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诗十九首》是中国诗歌史上辉煌的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