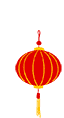我的家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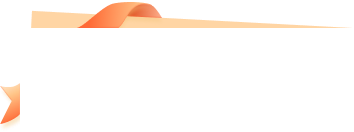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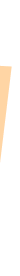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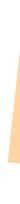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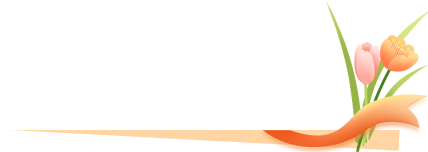
这里,是我的家乡,是我出生的地方。
我,在这里蹒跚学步,在这里长大。它,是我所有童年记忆的归属地,也是我心里永不磨灭的家。
小时候,我总嫌弃这层层叠叠的山峦,也总嫌弃从懂事就开始的砍柴、割猪草、插秧、种玉米、养猪、养鸡、养小鸭子……
那个时候,我特别讨厌干农活,总向往山外的世界。终于,我长大了,在这种理想中颠沛流离、疲惫不堪。让我没想到的是,只有这里,才给了我太多的爱和宽容:以前我总嫌弃家乡苍老破旧,可家乡从未嫌弃我年少无知;长大后总埋怨家乡离得太远,可家乡却从未埋怨我迟滞不归;我把骄横无理留给了家乡,把谦卑有礼送给了远方……
家乡,从未嫌弃过我。
我还想说,它从未离开过我。
相比于大城市里的繁华,我更加喜欢这里的宁静。有人说这里是世外桃源,也有人说这里是穷乡僻壤。生我养我的地方,再穷我都爱它。
在这里,很多人没有坐过地铁,甚至这辈子都没有感受过北上广的霓虹。手机更新到了第几代,他们不关心;拿铁到底加不加糖,也根本就点缀不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穿着朴素,用肩膀扛起了祖辈的传承,用勤劳的双手在风雨里劳作。他们每天在鸡鸣犬吠中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在袅袅炊烟中等待日出日落,看山川望远,只为自然农耕收获那最纯洁的食物。
在别人眼里,这是非常平淡无味的生活,可这里却还有许多人在这平淡的生活中演绎着平淡的人生。
这就是我的家乡。
我爱我的家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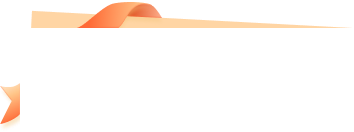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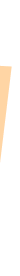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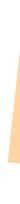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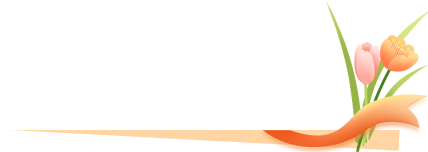
儿时的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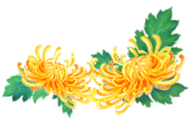
小时候,我常常看到菊姑婆抱着襁褓中的孙子坐在自家朝门口,边晒太阳边做游戏。只见她握着孩子的小手,把两根小食指捋直了,轻轻地点在一起,然后迅速拿开,俩小手臂一张一合,口里唱着《虫虫飞》:
“虫虫虫虫飞,虫虫虫虫走,一走走到嘎嘎大门口,舅妈放出一条大花狗。舅舅拿大烧饼来赶狗,险些把亲外甥咬一口。”
唱完,也不管孩子听懂没有,只见孩子笑了,奶奶也笑了,脸上满是慈爱。
我小时候没有见过奶奶,也不知道妈妈教我做过这样的游戏没有。我想,妈妈肯定没有教我做过这样的游戏,因为她是公社壮年社员,每天除了给我们浆衣洗裳、侍候全家人一日三餐,还要喂鸡养猪,更重要的是她每天都要参加生产队里的劳作,还要抽空种自家的菜园和自留地。她肯定没有时间来教我做游戏。
看到菊姑婆这样耐心的和孙子玩游戏,我心里非常羡慕,恨不得那怀中的孩子就是自己。
在孙子咿呀学语的时候,菊姑婆又一边打着节拍,一边教孙子唱《颠倒歌》:
"鸡公尾(yi)巴拖呀拖,听我唱个颠倒歌。爹过喜会我打锣,妈过喜会我抬盒,打从嘎嘎门前过,嘎嘎还在睡摇窝.手里拿块苦荞粑,屁股糊得像黄蜡。"
诙谐的《颠倒歌》听得我和小朋友们都哈哈大笑……
除了《颠倒歌》,菊姑婆还教她孙子唱《一生不走嘎嘎哩哒》:
“白菜白,青菜青,我是嘎嘎的亲外甥。今天我去看嘎嘎,嘎嘎捉来鸡子杀,舅妈直把眼睛眨,舅舅说我是伢子噶。我包一提,伞一拿,一生不走嘎嘎哩哒。”
听她唱完《一生不走嘎嘎哩哒》,我们便好奇地问她:“姑婆、姑婆,世间真的有这样可恶的舅舅、舅妈吗?”她听了,也只是笑笑,并不作答。
或暗或明的月光下,孩子们一手拿着巴扇,一手拿着透明玻璃瓶,追赶着空中忽闪忽闪光亮。菊姑婆就一边轻轻拍打着怀中孩子的小衣裤,一边吟唱:
“萤火虫,挂灯笼,飞到西来飞到东,晚上飞到家门口,宝宝回家它来送。”
菊姑婆还教过她孙子一首叫做《野鸡公》的歌谣:
“野鸡公,背把jiōng(弓),上高山,看嘎公。嘎公吃的什么饭,吃的红米饭,什么红?蛋蛋红。什么蛋?鸡蛋。什么鸡?秤鸡。什么秤?官秤。什么官?爪母官……”
孩子渐渐长大,可以做一些律动游戏了。菊姑婆就把孙子放在自己的双腿上做”推磨“游戏。她让孩子面向自己,握着孩子双手,作一推一拉状,孩子也跟着一仰一伏,咯咯笑着。这样边推边唱:
”推个磨,拐个磨,推个粑粑黑不过,做的粑粑白不过。客来哒,筛茶喝,炊子嗙到后脑壳……“
……
五六岁大的小朋友聚在月亮下面《交朋友》。他们手拉手,或排成一排,或站成一圈,或看向月亮,或看向伙伴,一边蹦蹦跳跳,一边唱着歌谣:
“月亮巴巴跟我走,一走走到黄金口,你炒菜,我打酒,我俩交个好朋友。”
这是教孩子们要与人为善,多交朋友啊!
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有时候就喜欢搞怪。他们或站成一排,或挤在一起,其中一个人一边用手指指着其他小朋友“数数”,一边念念有词: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在家,打屁就是他。”
他每数一个数或者每念一个字,手指就变换着指向另一个小朋友。当他念最后一个字的字音落在谁身上时,他便认定对方就是那个放屁的人。当然那被“冤枉”的孩子肯定不服气,便红着脸梗着脖子分辨:“不是我。我没有放屁,是你害我的。”紧接着,众人便是哄然大笑。
松滋人说话喜欢方言加脏字眼,俗称“带口语”。什么“妈的”、“克老子哩、”“个雷姐哩”等等。孩子们也有样学样,而且在有人指教的时候,他们还有反驳的理由:“松滋人礼性大,不带口语不说话”。
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的第一支歌是“戴花要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
松滋人有关家乡习俗的还有一段歌谣,它反映了松滋人热情好客、彬彬有礼的精神风貌。
“松滋人,礼行大,进门就把椅子拿,毛坝烟,沙罐茶,开口就是哦嗬哪。
米饭好,酒菜佳,还把炖钵炉子架,家乡口味自己弄,自己弄的香喷哒。
问嘎嘎,问姨妈,问了大人问小伢,亲戚六眷都问好,还问隔壁两三家。”
2023年11月10日夜 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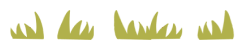

门前有条弯弯的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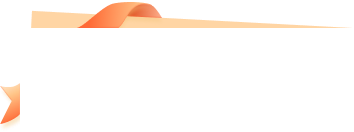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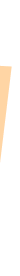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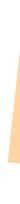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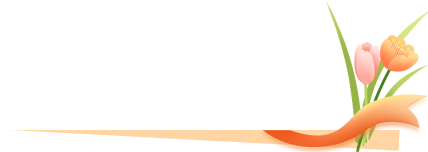
我家门前有一条弯弯的河,它就是洛溪河。
洛溪河是一条山溪河,处于武陵山余脉的末梢,由沿岸无数条大大小小的山溪汇流而成。越往上游,河道越窄,河水越小,卵石越大;越往下游,河道越宽,河水也越大,卵石越小;到了马食口一带,河滩上就只有瓜米石了,再往下游,河滩上就只有细沙了。
洛溪河大体上是由西北向东南流淌。在刘家场镇以寨子山脚下的象鼻咀为节点向上游呈Y字形分成两股主要支流,北边一支经官渡坪、大河口上朔至宜都市的松木坪、陈家河及以上广大山区;南边一支经觅水桥、在柳林河向上又分为两支,一支经傅家冲向上往水岩屋、吴家包以及东壁岩方向的广大山区延伸,另一支经山溪口向桃树、山望坡广大山区延伸。南边一支两岸都是石山,北边一支以大河口为节点,其上游两岸都是怪石嶙峋、悬崖峭壁,往下游到斑竹寺止,以河床为界,河岸北侧都是麻砂山(据说麻砂又叫作页岩),南岸都是比较平缓的岩石山。走出街河市地界,它才算走出了山区,直到流入洈水、注入松西河。
洛溪河也叫洛河。它在不同的地段还有不同的名称。在461电厂(大河口)到松木坪段叫干沟河,在刘家场西一支叫柳林河,往下农机厂(刘家湾)一段叫杜家河,鞍子岭易家台河段叫做李家河,小堰垱以下一段又叫梅溪河……
它平时很温顺,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不少便利,养育了两岸的百姓;孩童们下河捞鱼摸虾、在河滩上放牛牧羊、追鸟逐兔,尽情嬉耍,给孩子们带来无穷乐趣。但若是一到雨季山洪暴发,它就是另一副嘴脸,根本就是一头桀骜不驯的凶猛怪兽。不仅仅是阻断沿河两岸人们的交往,毁坏房屋、冲毁农田、破坏工农业生产、甚至剥夺人畜生命,它也没有少干过。所以说它有时候也会给两岸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听老人们讲,这条河曾经发生过两次特大洪水,一次是在戊午年,一次是在乙亥年。乙亥年也就是80多年前民国时期的乙亥年(1935年),而戊午年,已无可考证。据说兴家坪一条街就是在乙亥年的大洪水中消失的。当时冲毁房屋、田地无数,一些没来得及转移的人员和牲畜也被洪水卷走......也因为这次大洪水,我家门前的河道由北向南迁移了两百多米、变成了近似于现在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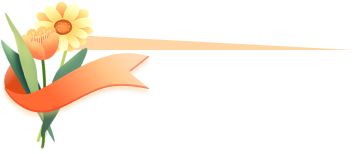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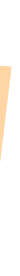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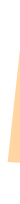

芒絮飘飘







我的家乡处在洛溪河的中上游。河床连同行洪道一起也只有一百多米宽,整个河谷的底部连同两岸的农田加在一起,最宽的地方才有大约1km、不到2km。平常的时候,河床的水面也只有三、五十米宽。河水也不是很深,除了一些深潭深坑外,绝大多数河滩水深只有20--30cm。在一些浅滩上,水深甚至不超过15cm。人们涉水过河也不是很不方便。
鹅卵石和泥沙构成的河滩上长满了一簇一簇的河芒和巴芒,岸边的细沙滩上长满了嫩绿的白茅草、狗牙根、木屐草,水边长满了水林草和毛蜡烛......河滩和沙滩构成了一片片天然牧场。这些沙滩、河滩和河水,伴随我度过了我的孩提时光。
河芒和巴芒,在我们这里统称为巴芒。它们无论是叶片的形态还是植株的高度,虽然远看极其相似,但是当你走近细瞧,它们还是有许多不同的。
巴芒的植株比河芒要高许多,茎秆也粗壮些,虽然都是长长的剑形叶,巴芒叶要肥许多。它们之间最大差异莫过于巴芒叶子边缘有非常锋利的锯齿。倘若你想收割它的嫩叶嫩芽来饲喂牛羊而又不戴上手套的话,分分钟都有可能把你的手剌得跟一只血肉模糊到血葫芦差不多。
河芒比巴芒就要内敛很多,看上去也瘦弱、秀气一些。它的剑叶没有巴芒叶那么肥厚宽大,植株也没有那么高大,叶片边缘更没有那锋利的锯齿。当然,牛羊对于它的兴趣也远远没有对巴芒的兴趣那么浓厚。由于河芒对于人体造成伤害的风险远远小于巴芒,所以,小伙伴们更喜欢在河芒丛中玩耍,而对巴芒却有一种天生的畏惧和抗拒。要不是牛羊喜欢啃食它的话,小伙伴们恐怕是一辈子也不愿意接触它。
巴芒和河芒除了嫩芽期可以饲喂牛羊外,也就只有等到秋后被人们砍来当柴火或者烧火粪。巴芒由于茎秆发达,晒干后又极易着火,所以,巴芒的茎秆是纸匠师傅扎制纸货工艺品的绝好原材料。
每年春天是生发的季节,河滩上一片葱绿,一派生机。到了夏天,河滩上则是一片墨绿,用郁郁葱葱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到了秋深,无论是河芒还是巴芒,它们都会黄叶、枯萎,到处一派肃杀之气,不再柔软的叶和花茎被瑟瑟秋风刮得呼呼作响。这时候的河滩真的跟芦花湖的景象有得一拼,巴芒的种子随着毛茸茸的絮毛在空中飘啊飘啊,飘向远方,像跳舞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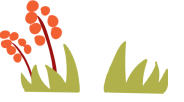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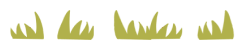

鸟鸣兔奔



每年的春天、初夏和秋天,河滩便成了小伙伴们的最爱。他们把牛儿放到河滩上吃草,人就穿梭在巴芒丛中。春天里掏鸟蛋,猜鸟,秋天里捉迷藏、追野兔.....
有时候,当你走近巴芒丛,总能听到一阵阵悦耳的鸟鸣声从附近的巴芒棵子里传来。如果循声找去,鸟鸣声又会从另一个地方传来。寻来寻去,就是找不到小鸟藏身何处。如是反复几次之后,小伙伴们也有些气馁了,干脆就不找了。于是就来竞猜过蒙。说来也巧,每当有人猜中小鸟所处的位置之后,那里的鸟儿就不叫了,鸟鸣声又会从另外的地方再次传来。这和之前的循声找鸟有异曲同工之妙,引起了小伙伴们的极大兴趣,以至于乐此不疲。
当然,最有趣的莫过于当你在巴芒丛中捉迷藏的时候,忽然就从巴芒棵子里蹿出一只野兔来。这时候小伙伴们就会放弃所有游戏去追野兔。大家叫着喊着,围追堵截、从这个棵子追到那个棵子,简直有些疯狂了。就是摔跤了,或者被磕伤了、割伤了也没有人在意,绝对没有人哭哭啼啼,只有欢笑声和尖叫声。
让人更兴奋的是追着追着,忽然不知从哪里又窜出一只野兔来,于是小伙伴们就自然而然地分成几拨人来追。也不知道那野兔是不是故意要削弱我们追击的力量而为之......那野兔也不往远处逃,就在附近的巴芒棵子里东多躲西藏,好像是在故意和小伙伴们捉迷藏似的。只可惜追着追着,就不见了野兔的踪影。最终,当然是一只野兔也没逮到,人却是累得不行,但是大家却从没有因为累而放弃这项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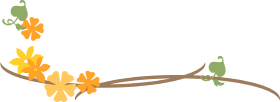
筒车悠悠


洛溪河岸边的车水筒车不仅仅是一种观赏景观,更是一种古老的农业自动提水机械。它是用木头做成的,跟现在一些景点的景观筒车极其相似,所不同的是车水筒车上除了在其最大圆周部位均匀地安装有许多宽大的木制叶片外,还安装有专门用于盛水的水桶。这些水桶,在安装的时候和叶片的状态稍有不同,叶片是水平安装的,而水桶则是呈60°角倾斜着的。在筒车向上运行的一侧看,水桶的桶口是向上倾斜着的。这样,水桶里的水在筒车向上运行过程中才不会流出来。根据河岸和河水落差高度的不同,筒车的大小也不同,有的直径有两三米,有的直径有4米左右。当然,三四米直径的筒车就算是很大的了。它的工作原理是依靠强大的水流作为动力冲击筒车外圆周上的叶片和水桶,使筒车随着水的流动而日夜不停地转动。当盛满河水的水桶转到最高处后再继续转向下方的时候,也就是在水桶翻山的时候,水桶里的水就会倒出来,流入专门建好的桶车码头的水槽里,经小渠流向农田。
筒车悠悠地转动,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传到农人的耳里,乐在农人的心里。农人们心里充满了对丰收的渴望和喜悦。
用筒车车水浇地,不用人力,不用燃油,不用电力,也不用畜力,更不需要多么复杂的机械设备,堪称中国农耕文明的一项伟大创造。据了解,用筒车车水浇地是从宋元时期传承下来的。它的主要缺陷在于:一是每次洪水过后,都要集中一定的人力到河里筑垱拦水,以恢复筒车的动力和给水系统;二是在大旱之年,河水减少,可能不能满足筒车的动力需求;三是一部筒车所能灌溉的农田面积有限,不能大范围浇灌。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我亲眼所见的车水筒车,也只有三处。一处在鸡公嘴对岸,属于当时的胜利五队所有;一处在瓦窑嘴对岸,属于当时的胜利三队所有;还有一处在我家对面的河岸边,属于水槽子所有。不过,在沿河两岸倒是存有不少车水桶车码头的遗迹。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有了压水机(一种以水能为动力的涡轮水泵),车水筒车才真正退出农业生产的历史舞台。
从此,车水筒车也就成了我儿时的记忆。


水利设施的过往



引洛溪河水浇地,在旧时,车水桶车可能是沿河两岸唯一的大型自动化提水设施了。在那种小农经济模式下,要集中人力物力去拦河筑坝、引水浇地,其难度是可以想见的。人民公社化后,在肖家坪公社的支持下,松竹大队、四盟大队曾联手在岩屋咀河段开山炸石、修筑了洛溪河上第一条简易拦河坝--大垱,开渠引水浇灌四口堰、兴家坪一带河谷地带的农田。然而,因为每次大洪水之后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来修复大垱,所以没过多久,这座大垱便被遗弃了。到了八十年代,白鹤山人又才举全村之力,重建了这座水利设施,将之建成了一座由块石加水泥浆砌而成的滚水大坝。
洛溪河上第一条比较坚固的滚水坝当属于始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马食口滚水坝;工程规模最大的滚水坝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由原松滋县政府牵头兴建的大河口黑冲子滚水坝,其引水渠逢山钻洞,逢谷填方,蜿蜒30余华里延伸到南河水库;同时期乐园大队在倒拐子湾那里兴建的乐园滚水坝也算得上是一项较大的水利工程。
这些水利设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曾经或正在为当地的农业生产发挥着巨大作用。
说起洛溪河上的水利工程,不得不讲讲梨山咀洛河改道造田工程。这是一项由原斯家场公社党委书记郑永传动议、经松滋县委批准动工的工程,而且最终还是一项烂尾工程。
此工程于1976年秋开工,其目的是挖断栗山咀,将原本绕道栗山咀西侧北去、经月亮山脚下后又向南绕回栗山咀东侧的大竹园的河道取直,然后在关王庙到栗山咀之间拦河筑坝,引洛溪河水入新河道到大竹园进入旧河道,并将原河道及其沙滩平整、改造成水浇地。工程预计开挖土石方75万立方米;筑河堤1.5公里,土石方18万立方米;筑拦河坝1公里,土石方30万立方米(这些还没计算整治河滩造地的工程量);需占耕地180亩,可造耕地560亩。(当时,公社党委还规划,在此项工程顺利完成后还要继续在赵家台实施规模更大的洛河改道造田工程。)该工程在没有任何大型施工机具的情况下,动用了全公社18个大队的部分劳动力(大部分劳动力在县办水利工程文家河水库工地施工),每天大约600人,全凭用锄头挖,用扁担挑,用手推车推等原始办法干了4个冬春,用工约15万个,也只是让新河道初具规模,拦河大坝根本就没开工。后来由于毛主席去世,“农业学大寨”的热浪渐渐冷却,接着大家都去争当“好猫”、“向钱看”了。此项工程最终不了了之,办成了劳民伤财的烂尾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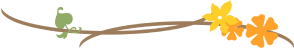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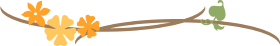
人间仙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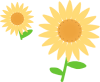

我喜欢看炊烟。每天早晨,无论是在河坝放牛,还是在山上割草,都能看到从千家万户的烟囱里或瓦片缝里升起的缕缕炊烟。没风的时候,炊烟像一根根柱子,袅袅落落,缓缓地插向天际;微风的时候,炊烟又像一片片薄云,飘飘荡荡,慢慢的连成一片,笼罩在房屋和半山腰间,像长长的绢,又像绵绵的桥,飘飘渺渺、伸向远方。这时候,我就会望着那绢、那桥怔怔发呆,心想:这世间究竟有没有神仙和仙境啊?若有,那它们在哪里呢?若没有,那这些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仙境呢?这样说来,我们岂不是正生活在这仙境之中吗?……
我喜欢炊烟,除了它那令人遐想的美,还因为它是给我们报时的信号。早晨,屋顶的炊烟渐渐淡去的时候,仿佛是在告诉我们:妈妈的饭熟了,赶快回家吧,要上学了;傍晚,屋顶的炊烟慢慢消失的时候,好像在催促我们:倦鸟要归林了,妈妈正盼儿回家呢。
我喜欢炊烟,更因为有炊烟的地方,就一定有人类活动,就一定是个好地方。拨开袅袅炊烟,便能见到人们战天斗地、生龙活虎、生气勃勃景象。
我喜欢炊烟,我爱我的家乡。
可惜啊,现在想再见炊烟,已经成了一种奢望。

黑屏墙 我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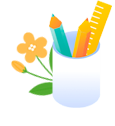

北方古建筑




黑屏墙原本是一处建筑物,并不是一个地名。可能是因为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它是这一带为数不多且较为宏大的建筑,带有地理标志的特点,人们就把这个地方也称为黑屏墙了。至于这个地方最原始的地名叫什么,现在没人知道,也没法考证。不过,据史料记载,黑屏墙后面的小山叫做君顶山。现在知道的人并不多。
黑屏墙大约是明朝时期遗留下来的一座老建筑。
根据遗迹判断,屏墙建筑大致坐南朝北、偏向东北方向,东西开间,和南北进深各约20m见方,加上四周的围屋,总体约50m见方的样子,呈典型的四水归池的古“八大间”建筑。四面的墙壁是一种用古老的青砖和石灰浆砌成的斗墙。传说那石灰浆根本就不是什么石灰浆,而是糯米浆。由此也可以感受到当时主人的富有和对建筑质量的高要求。
屏墙建筑内部呈九宫格式布局,分为上、中、下三进,头进房称作下堂屋和下房,上进房称作上堂屋和上房。上堂屋、下堂屋左右两侧的房间称作正房,中进房正中是一口大天井,左右两侧的房间称作“厢房”。
屏墙建筑的入口(大门)在下堂屋。大门的门框、门顶、门槛由四块巨大的条石打磨而成,门槛外边还有一块长1.2m、宽0.6m、厚 0.3 m的踏脚石,但是门前没有高高的石台阶,也没有门鼓、狮子或者貔貅等装饰性建筑。穿过下堂屋到达建筑的中心,便是那硕大的天井,穿过天井就是上堂屋了。天井的池底用刻着花纹的青石板铺就,天井靠上堂屋一方的坎是用正面雕刻着虫鱼鸟兽和花卉、云纹图案的块石砌成的。古人建房讲究风水,屋面上的水落下来也讲究四水归池。水则象征着财源、财气,那天井就是一个聚宝盆。天井里水经地下荫剅向东、南、北、西四个方向的明阳沟排出。鸟瞰的话,其四水归池的建筑结构跟图片中北方古建筑的样子很相似,只是规模略小。
下堂屋的地坪比较低,但比天井的地面要高出20cm的样子,上堂屋的地坪比天井的地坪要高出60cm左右。从下堂屋进入天井,有一道大约40cm高的石门槛,从天井到上堂屋则要通过一座三级的石台阶。大有步步高升的寓意。
这里的天井跟别处的天井有所不同,别处的天井只是房间的中间部位有池子,可以落水、集水,周边都有可以供人行走的通道;这里的天井是一整间房都是落水、集水的池子。我们小时候也管它叫做“池子”。要想从下堂屋到达上堂屋,就必须从池子中间穿过去。
其实,在我儿时眼中的黑屏墙,不过就是在一些断壁残垣上用土砖垒起来的土木结构建筑。虽然根据建筑的轮廓来看,占地面积还是那么大,天井也还在,但丝毫不见当初的豪华气派。怎么看都给人一种衰败萎靡之气的印象。
屏墙的墙壁下半截还是那种薄薄的青砖斗墙,上半截却是土砖了。原本用条石矗立起来的大门框也只剩下了一半,屋顶也破败的七零八落,“走马转过楼”已然不复存在。所见的只是一些横七竖八的零乱房屋。听老人们说,这都是老东(日本鬼子)给祸害的。是日本鬼子一把火把那传说中大气、豪华的黑屏墙给烧成了废墟!后来经过土著居民在断壁残垣上修整、搭建,才有了我眼中的黑屏墙。
在屏墙建筑的东、西两侧还还能见到不少围屋,是东家供长工们栖身的那种围屋。我们家是刚解放的时候(大概是1950年)迁入黑屏墙的,住的就是那种围屋。
儿时,我和小伙伴们在天井那里玩耍的时候,分明还见到过下堂屋靠近天井外面的左右两侧耸立着一对用白色石头琢磨而就的磉磴,不过也是炸裂得满目疮痍了。据传说,那白色石头叫作“白瓜石”。这白瓜石磉磴则是远在湖南天门山的易氏賡公元配夫人“皮氏太太”命人从四川葵花井运来送给曾孙子落成之喜的贺礼,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那白瓜石磉磴之所以满目疮痍,听老人们说,这还是日本鬼子造的孽。那把大火不仅烧毁了这里的房屋,连那对珍贵的白瓜石磉磴也没能幸免,被烧得四分五裂、面目全非了。
小时候,我经常到玩伴们家里去玩,也喜欢和他们一起在他们家里到处钻来钻去、捉迷藏。我记得,炎叔家的老房子虽然是从围屋向西出进的,卧室可是在老八大间的正房,所以,卧室里是有阁楼的。木制阁楼楼层很高,通过一张笨拙的大板梯可以登上阁楼。阁楼上面很宽敞,三面都是墙壁,向东的一面是用很精致的木格栅做的隔断。靠西侧的墙壁上还有一孔不算大的拱形窗户。据说那是过去大户人家小姐的“绣楼”。这也是这座老建筑中残存的唯一的“绣楼”。听老人们说,在没有被老东烧毁之前,屏墙建筑的整个二楼是可以相通的,叫作“走马转过楼”。
在屏墙建筑的东侧,有一盘巨大的石碾子。在石碾子再往东一点,有一口大约五亩水面的呈宝葫芦形状的大堰塘,大堰塘再往东边的坝子上有一座叫做新新庄土地分下张李二爷土地的小土地庙。
黑屏墙的大堰,也算得上是一处地理标志,跟什么“四口堰”、”七根柳“、“一步四个田角”、“三步两道桥”、“一步踏三县”一样齐名。过去,人们出行,没有现代交通工具,主要靠步行。如果行程很远,又想随时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你可以不知道当地具体的真实地名,但这些地理标志却不得不时时留意。
黑屏墙的大堰之所以闻名,一是因为它的大,水面在5亩左右。这在从刘家场到新江口古道沿途绝无仅有。二是由于引泉水湾山泉灌注,水质清澈见底,甘甜可口,水面上没有一点漂浮物。蓝天、白云倒映在水面上,虚幻而又真实。三是因为它就在大路边,甚至有一段路就是大堰的堰堤。南来北往的行人、马帮来到这里,渴了、乏了,都可以在这里驻足小憩,拘一抔甘甜的塘水。
相传,以前,大堰塘的四周都是建有围墙的,而且围墙可能还很高。旧时候的妇女是不可以抛头露面的,更是不可以随便给人看见的。据传,曾经因为有一个骑着骡子的驮夫从围墙边路过,瞥见了围墙里面妇人头上的缵边,主人就下令将围墙又加高了三斗。
可惜了,现在,这里的屏墙、绣楼、围墙、石碾子……早已成了传说


碓码 石碾


在没有打米机、磨面机等现代化粮食加工机械的年代,石碾、欙子、碓码、石磨就是人们加工粮食的重要设备。
穷家小户的,粮食的用量也不大,就拿稻谷来用樏子樏、用碓臼舂,然后用簸箕簸、风车车、用大筛、隔筛筛,就可以了。而大户人家,家人、长工什么的,随便一聚就是十几人、几十人吃饭,粮食的用量就比较大。若是年头时节、生日满月、红白喜事、传统节日等等,粮食用量更大,品类也更多。这种情况下,如果还用樏子、碓臼、石磨这些设备来加工粮食,就会显得力不从心,所以石碾子就派上用场了。当然了,用石碾子加工粮食也不是大户人家的专利。哪怕是穷家小户,只要实在有需求,也是可以用石碾子来加工粮食的。
到了现代,有了打米机、磨面机等粮食加工机械,碾子、碓臼才慢慢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不过,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一些榨油作坊都还可以见到石碾子的身影。直到九十年代,有了液压榨油机、对辊机,石碾子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是,哪怕是到了今天,虽然这些设备已经成为传说,但在一些偏僻的村落里,仍然可以见到碓臼、碓码的踪影。



黑屏墙的石碾子 示意图



黑屏墙的石碾子与影视作品中见到的石碾子有所不同。影视作品中的石碾子大多由一面巨大的石碾盘和一个石头磙轮构成,靠人力或畜力推动或者拉动,且石碾盘要高出地面许多。
黑屏墙的石碾子大体上由碾心、碾槽、碾枷、碾辊几部分组成,靠畜力拉动。它没有象磨盘一样的大碾盘。它的碾盘是有许多块掩埋在地面下的石头U形槽拼接而成的一个正圆形碾槽,大体上与地面持平。
从平面上看,碾盘是一个划有圆心的、直径为2.5米--2.8米左右的圆。圆心就是碾心,是一块半截埋在地下半截露出地面的圆台体的石头,顶部凿有一个10厘米见方的孔洞,孔洞里打入一根下方上圆的木桩,用以固定碾架的顶端;碾盘的圆周是由数块被凿成弧形的石碾槽拼接而成的。弧形的石碾槽顶部凿有上宽25厘米、底宽15厘米、深25厘米的U型槽,一块一块的U型槽拼接成一个圆周,我们叫它碾槽子。碾枷是用两根长度略大于石碾盘半径、粗细不低于15厘米见方的方木做成的A字型的架子。把A字的顶端固定在碾心上,在A字的两脚处分别安装上直径约为60厘米、厚度约5-7厘米的砂石轮,这一盘石碾子就成了。这砂石轮就叫做碾辊(磙)。
人们往碾槽子里装入适量的稻谷或者大麦、蒸谷子等,然后在A字型碾枷的左脚侧套上缆索、革头(gétou, 原本在我们当地gé头的gé,写作左右结构:“轭(读e)”和打匠木,用耕牛或者骡子、驴子拉着碾子逆时针方向绕碾槽子行走,碾磙则在碾槽子碾来碾去。用不了多久,碾槽子里粮食就会被碾熟、甚至被碾成粉。直到达到要求才起碾,然后又重新再来。有时候,如果觉得碾子太轻,或者说是效率太低,人们还会在碾枷上压上一大块条石,或者坐上几个人,给碾子配重,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我小时候跟着大人去碾米,就喜欢坐在碾枷上给碾子配重的那种感觉,就像坐车一样,不停地往前运动,还不用使力气。
以上是我儿时见到的和从老人们的传说中听到的黑屏墙。时代发展到今天,旧时的八大间建筑已然不复存在,有的只是那些少得可怜的传说和遗迹,还有一些可以佐证这些传说的地名、田名和山名。在其遗址及其周边,耸立着一幢幢小洋楼,一条水泥村道伸向远方。
昔日的古道早已没了踪影,连同其一起消失的还有那牵骡子、骑马、赶驴子的驮夫、驮队以及肩挑手拧的小商小贩和行人来去匆匆的身影。那牲口的铃铛声、小货郎的铃鼓声,统统地、永远地停留在了我儿时的记忆里。


黑屏墙这地方也曾是一方风水宝地。她背靠青山松林坡、军顶山,北临绿水洛溪河,西枕松南屏障,东边有桂花台和与之隔河相望的关王庙相守,门前一条古道西通鄂西南门户刘家场古镇,东达古渡口划子嘴,左首不到一华里的地方便是古驿道乡集兴家坪(俗称肖家坪),东行七华里则是古驿道乡集鞍子岭,向南四华里就到达了杨家溶过街楼,往南再行十五华里便是松滋著名的南五场之一的松南古镇西斋。
这是一个要山得山要水得水的好地方。最重要的是这里柴方水便、农业生产十分便利。水浇梯田层层叠叠从洛河边一直延伸到门前的打场边,并引压榨湾泉水予以浇灌,基本上旱涝保收无灾年。
相传,黑屏墙原本不叫“黑屏墙”,而是叫“金屏墙”。据传说,黑屏墙的屏墙建筑刚刚落成的时候,那建筑是散发着金色祥光的。而且每逢月圆之夜的子时,都会有一匹金马降临天井“饮水”、“吃料”。久而久之,这个秘密还是被人发现了。于是有人就起了贪念,欲将那金马据为己有,便纠集人手打算擒住金马。不料弄巧成拙,金马没擒住,反而惊走了金马。从此那金马一去永不复返,那原本散发着祥光的金屏墙也从此变成了黑屏墙。
这虽然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是否真有其事也无从考证,但却明明明白白地告诫人们:做人是不可以贪得无厌的。贪得无厌只会失去得更多。
黑屏墙由“金屏墙”变成“黑屏墙”的原因还有第二种说法,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军在附近挖了一条几米宽3、4米深的防御战壕,从而挖断了龙脉,破坏了风水。这个近代传说,同样也说明了一个事实:战争的创伤永远无法愈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