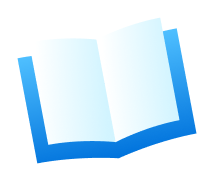

每年清明前后,春雨绵绵之时,在属于自己独有的时空里,我总是放飞哀思,怀想、追忆和祭祀已故亲人。伯父就是我时常缅怀的一位故人。
伯父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然而,他那布满沧桑的脸庞、以及我和他一起战天斗地走过的那些往昔,时时铭刻在我的心头,令我忘怀不得、、、
伯父生在曾祖父为避贼难而举家迁移到现村的两年后。为了生计,伯父从小就为地主放牛、打长工。因劳累过度且无钱医治,伯父年轻时右眼便已失明,没到中年,左眼又上青光,行动十分不便,但是为贫所迫,伯父一直手握锄头劳作不止。
分田到户前,才十岁光景的我,因母亲去世家境贫困,开始扛着一把比自己还高的锄头到生产队劳动谋生,日工值3分。秋冬时节,我能做的工是种杂粮、挖红薯分红薯等轻便工;春夏两季,队里安排我早晚整田埂,周末插田。同我一起整田埂的是几位体弱老者,大伯父便是其中之一。山区的田埂高低不一,高的四五米,矮的几十公分,整草时有的人在垄上用长刀砍,有的人在田中用锄头钩。田里的蚂蝗多,我和伯父属于更弱势的人群,只能在下面挖钩了。伯父做工向来自觉勤奋卖力,常常做完一大段又过来帮我做,待我俩做完工上岸后,伯父常因看不清而被两三条蚂蝗扒到脚上吸血胀鼓鼓的。我见后赶紧帮伯父捉蚂蝗,并马上找几种山草药芯嚼碎敷到伯父伤口上止血。大锅饭时代,出工迟,收工也晚,伯侄俩一老一少多是披星带月踏着山道弯弯的乡间小路归家。十岁光景的我望着风吹草木影影卓卓的黑夜,常问伯父:“那是不是鬼?”伯父总是安慰我:“那是树影,你不必怕,即使有鬼,我也能打走它,放心吧。”在伯父的帮助和护卫下,我渐渐的大胆起来、、、
夏收秋收很长一段时间,队里的谷物都需要几人晚上看管。看守一晚得4分工。有家室的人都不太愿到远离村庄的晒谷场守夜。未能成家的伯父不嫌辛苦,长期当守谷人。1980~1981年,我也加入守谷人行列。每天晚饭后,我照着手电,牵着大伯行2里山路到谷场守夜。不管是月明星稀还是风狂雨急,一任那些艰苦的时光伴着我2年多、、、
春雨夏日,星移斗转,伯侄俩顶草笠,背蓑衣,一直相依携手做工到1982年底分田到户止。
1982年9月,我去镇上读中学,三年后到省城念大学,毕业后到钦州市区工作。我每次回家看望父亲时,见伯父都感到他苍老很快,百忙中,我总是抽出时间和他小坐拉家常,对人生深感无助的大伯,常常久久不语、、、
九十年代初,为了生计,已近失明的七十多岁的大伯,仍不得不修田埂,整坡地等,工余时,伯父大多是拿一张矮凳,在屋檐或者树根下寂寞静坐、、、
那时,仍为钱所困的我,除了春节给一百几十块钱贺岁钱和些少不成样的礼物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待到我境况好些,想好好报答他时,他老人家已不幸去世。每每想起此事,我满怀惭愧,满心酸楚、、、
受尽人间悲苦的大伯早已离我远去,但伯侄俩战天斗地的情景,携手走过的蹉跎岁月,仿佛就在眼前;伯父默默忍受,从不怨天尤人的人生态度,勤劳卖力、风里来雨里去的身影,常常激励着逆境中的我去迎难打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