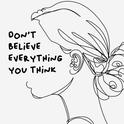张治云
安长庚老舅是我奶奶的亲叔伯弟弟,与爷爷奶奶家同在沁源县城关镇城西村居住,两家来往走动非常亲近。老舅家院子在县城中宣街路南,家族内简称南院。城内安姓家族素以耕读传家、知书达礼、为人正直而称道。
我从小跟着爷爷奶奶在家乡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对安长庚老舅也很熟悉。每到逢年过节,或平时有什么事情,奶奶总要吩咐我:“去南院你老舅家一趟”。
老舅的小院
老舅家的院门朝西开着,青砖铺院,整洁利落。正房三间两层,一楼住人,屋内永远是窗明机净一尘不染的舒适空间。二楼是仓库,存放粮食、农具等。院子东侧、南侧均是老宅基地,被日本鬼子烧毁后,一直没有能力修复,但也没有荒废,在勤劳者的手里,肯定会物尽其用,老宅基地开垦为小菜园耕种甚好。在小菜园外堰的砖墙上,种植着各种各样的花草,如月季花、绣球花、菊花、水红花、马兰花等等,春夏秋三季,小院里总是姹紫嫣红,花香四溢。小菜园里,有西红柿、黄瓜、茄子、豆角、北瓜、小葱、韭菜、金针等应季蔬菜,那可全是纯天然无公害的绿色蔬菜噢。有一份付出,就会有一份收获。这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农家生活自是一种陶冶。一看这个小院子,就感觉主人是有品味、爱生活的劳动者。
半个窝窝头
我记得与南院老舅第一次亲密接触,是1960年春夏之交,农村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人人都在饿肚子。当时农村公社化,还在吃大灶饭,我家院子有三间西房被村里征用为集体食堂,每到吃饭时间,社员们都排着队打饭,小孩子们都好奇地盯着大人们碗里盛的什么食物。有一天中午,老舅打饭出来正遇着我和几个邻居小孩在院子里玩,只见老舅喊了我一声,便蹲下来,隨手将筷子挑着的两个窝窝头,掰了半个塞到我手里。我当时看见那只大粗碗中盛着稀汤瓜水的调和饭,还飘着蓝天白云的影子。这就是老舅和老妗的午饭啊。
我回去将老舅给我窝头的事告诉了奶奶,奶奶提醒我说:“你吃了老舅的干粮,老舅就要挨饿了。”老舅当时还是生产队的壮劳力呢。
我还记得,每当北京安世祥老舅来信,或者福建天恩叔以及西安牡莲姑来信,南院老舅总要来与爷爷奶奶共同分享,煮茶聊天,遥祝远方的亲人幸福安康。
太岳山上采蘑菇
我上小学六年级时,因文革停课,奶奶曾让我跟着南院老舅上山采蘑菇、担柴。在夏秋之交,雨过天晴的时候,我们爷孙俩一人挑一对箩筐,大约要爬20里山路。路上,老舅会讲安氏家族的故事,讲他抗日战争时期参加百团大战的故事,讲福建、西安子女们的故事。我们一边爬山,一边讲故事,一边欣赏山水风景,偶尔还会与野山羊、野狍子、野山鸡友好相遇,不知不觉就钻进了茂密的太岳山森林里,伴着松风,听着鸟鸣,采摘鲜嫩的松蘑、山金针、山木耳等山货。中午,我们吃着黄生生的烤窝窝头,喝着甘甜的山泉水,别是一种乐趣。当我们满载而归的时候,老舅会给我讲述沁源军民围困日寇两年半的悲壮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八万人的沁源,特别是县城的老百姓,遭受日本鬼子屠戮最严重,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整个县城的房屋全被烧毁,家家都有血泪账,家家都有参军参战的勇士。英雄的沁源军民团结一致,运用人民战争、持久战、游击战等战略战术,终于在1945年4月11日将日本鬼子赶出了沁源。在抗日战争期间,沁源没有出一个汉奸,没有一个村维持敌人,这在中国抗战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整个二战时期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沁源人民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资本。
我们一路肩挑蹒跚,一路回顾历史,南院老舅用他坚韧不拔的意志,用他豁达乐观的人生观熏陶着我童稚的心灵。
以后,我到长治读书、工作,每年春节都要回家乡探望爷爷奶奶和南院老舅。他老人家已经古稀之年,身体依然很健硕,而且还坚持参加生产劳动,更让我惊讶的是还坚持上山担柴,那可是青壮年的活气啊!老舅说:“在家闲着坐不住,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当是锻炼身体哩。”
1975年春,我奶奶病重期间,南院老舅几乎每天前去探视安慰。奶奶病故后,老舅自始至终参与了后事料理。老人家还让我看他的记事本,记录着长辈们的生卒之时,记录着晚辈们的生辰之日,甚至连我父亲兄弟们的生日也记得一清二楚。可见亲情诚可贵啊!
他老人家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但他刚直不阿的腰板,慈眉善目的容颜,吃苦耐劳的精神,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2023.1.5日于潞州
前排中为作者,1957年摄于长治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