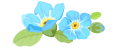小时候家里穷,每逢母亲到韩城赶集,总是哭着喊着要跟,原因很简单:母亲赶完集总会赏我这个跟屁虫一个锅盔馍。韩城的锅盔馍外焦里嫩,上面的面旋儿间还有一些芝麻粒。母亲忍饥挨饿不舍得吃,我却能双手抱馍先抠馍旋儿入嘴品味,紧接着一头扎进馍里啃得咯嘣儿咯嘣儿香。




母亲节衣缩食惯了,她每次赶集除了购买家里的必须品外,从不舍得狂花一分钱。虽然母亲对自己很苛刻,但是对于我,她还是照顾有加的。拟或有时母亲粜粮食多卖了几毛钱,她就会亳不犹豫地跑去韩城冻糕那里给我称上二两猪头糕夹在热馍里。我总会双手抱馍,像个迎接女贵宾的绅士,先有风度地照着馍亲一下,再用小眼儿环视一下周围,使劲目䁖一下群众,然后伸出舌头缓缓舔食着馍缝中的肉沫儿,强忍着满口的哈拉子水久久不舍得将馍吃完。




小时候去韩城赶集多跑路。母亲一手扶着肩上的粮食袋,一手扯着我的小手。近二十里地的路程,要是幸运有顺路的牛车什么的趁段儿还好点儿,要是点儿背就得一个劲儿地走了。尽管如此,我一想到母亲赶完集有好吃的就铆足了力气。




韩城的羊杂割一直是我儿时的梦想。为了生活,父亲常年出外打工,那时没有微信、支付宝,一年到头少得可怜的几块钱工钱都是随身带回家的。当然,每到年关父亲回来,我就会透透彻彻地解一下馋。




像现在一样想去喝就去喝是不可能的。父亲回来得去办年货,我们兄妹几个才有机会去解谗。问题是路远交通不便,去韩城是有事儿不是去玩儿,所以大家争得脸红耳耻也不见得能去。妹妹小跑不动不能带,哥哥们大了带着不好看,母亲不让去,我不大不小自然就成了幸运的当选者。




临近年关,天寒地冻。冷冽的西北风将我的小脸蛋冻得发紫发红,两行清鼻涕像刚下的粉条在嘴唇上下来回窜游,甚至吸不及时会舔入口中。但羊杂割的香味儿让我在冷风中像铁了心的勇士义无反顾。




跟着母亲转街也是体力活儿。母亲要办年货,满街寻长问短贪图物品的物美价廉,而我却得陪她东跑西跑走得叫苦连天。
韩城街上的羊肉汤馆很多,热气腾腾的香味飘得满大街小巷都是,害得我望眼欲穿,喉咙里的哈拉水像雨后山泉般一个劲儿泛滥。




两毛钱的羊杂割也不是随便能喝上的。只有母亲掐摸着赶集会到晌午跟不上回家吃饭时才会留下来喝汤。母亲不舍得吃锅盔馍,在买汤时常常只给我买个锅盔馍,而自己却把家中带来的烙馍就汤吃。




不管怎么说,只要母亲让我跟她一块儿去喝羊杂割,我便会亳不客气地尊贵入席。别看我年纪不大,喝羊杂割,我是很有方法的。先啃一口锅盔馍,再用小嘴对着大瓷碗汤面吹几口“仙气”,等汤面上的葱花儿和香菜花儿不耐烦地荡漾到碗的另一侧,我便把小嘴儿浸在汤中狂吸一阵子。汤中的羊血好嚼,我就用门牙叼切而食,对于羊脆骨,我会用大牙将其咬得咯崩儿咯崩儿响……喝汤时候的我从不讲究吃像,也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总是把自己弄得满嘴满脸都是油渣儿和馍渣儿。那小猪争食般的吃法总把母亲吓得够呛,她时常还得劝我慢慢吃以免噎着。




喝羊杂割的肉要钱,而添汤不要钱,所以,我总会哧溜哧溜先喝一碗汤垫肚底,再加的汤才算正式入席宴。往往喝一回羊杂割要把肚袋擞抖多遍,唯恐两毛钱花得亏了。




儿时韩城羊杂割的味儿是无法用言语表述的,它充斥着我的记忆已经几十年光景没有什么可代替了。也许那个时代的羊杂割确实够味儿,它影响着那个时代人的记忆已不是我个人的口碑所能及了。




如今乡村巨变,记忆中的韩城街早已旧貌换新颜,儿时的羊杂割汤馆馆址也几经变迁,故地重游时很难找寻到往昔的影子,但无论我身在何方,韩城锅盔馍和羊杂割的味儿依然能够历久弥香。




韩城的味道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丰富多彩起来。韩城牛肉汤、王殿子烧鸡、秦王古酒、张作帅红薯制品、大秦人家的菜、韩城水蜜桃、于凹金梨等,都让南来北往的人们贪恋其中,爱慕有加,韩城味道也在逐渐走出宜阳走向全国。




在韩城人的努力下,韩城正以宜阳副中心新姿态在各乡镇中崭露头角,韩城美味也逐渐成为宜阳人深铭于心的惦念,但凡到宜阳旅行的人要问吃什么,宜阳人都会自豪地说“到韩城喝羊肉汤去。”韩城味道渐而引领了宜阳味道。韩城这座千年古城不仅焕发了她昔日的繁华喧嚣,也正在以勃勃生机迎接着四面八方宾朋的到来。




作者简介:闫红岩,河南省宜阳县人。曾先后任河北省诗友联谊报社记者、石家庄市少年智力开发报社特约通讯员、江西金太阳教育集团特约编辑等。在省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百余篇,2018年一2019年修编江西金太阳教育集团《益学程》七八年级历史教师教参3部。待出版作品有诗集《自然传启》、论著《形形色色的教育案例》、长篇小说《谈天唬地》《王邦瑞传奇》等,中篇小说《青梅》现于喜玛拉雅3个演播室热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