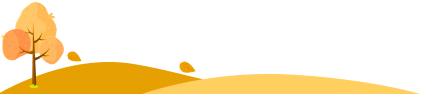离开老屋很多年,慢慢习惯了远离土地的日子。但是因为农村长大的缘故,总还是会经常想起自己在田园间生活的那些事情。
偶尔回老家,却无论如何找不到当初那些生活与劳作的模式了,很多原来属于农村的生产都已淘汰。社会在发展,很多东西也只能回想一下,更大点的作用大概就是写下来作为给儿子讲故事的素材了。
摘茶叶
摘茶叶这件事情,男孩子倒是很少做,但采摘回来的茶叶加工一般会要我参与:母亲把鲜嫩的茶叶放在大锅里炒熟,再倒在抹干净了的门板上,让我帮着揉制炒熟的茶叶,把鲜茶叶里的水分挤出一部分,并使叶片变成皴缩的形状。经过这道工序,再把茶叶平铺在茶炕(一种圆形竹编器物)上,在太阳底下晒一两天,碧绿的叶子就变成了黑色的干茶叶。
然后母亲把干茶叶装在袋子里,带到供销社的收购站里去卖掉,价格四时不同,每次也只有几斤干茶叶卖掉,但这却是补贴家用的一项重要来源,有时我们的学费也从中来一部分。
采茶一般在春分前后就开始了,因为我是和姐姐一起上学的,有时在放学后也会和她一起到茶园里去,看她和母亲双手在茶树上轻巧的移动,蜻蜓点水似的,一下子手里就有了大把嫩绿的茶芽——一把把的茶芽放到茶篮里,个把钟头不到就有满篮了。在那时而言,这就是一种收获的希望,因为采茶是家里一项很重要的副业。
采茶的时候,也是竹笋和蕨出土的季节,茶园的土是每年都要翻整和施肥的,因此蕨和笋也都会在茶园里长得很壮硕,在采茶之时,常常顺带挖几支竹笋或者掐一把嫩蕨回去。晚餐就有很新鲜的野味小菜了:竹笋可以新鲜炒腊肉吃,嫩脆清甜;而蕨用开水焯一下,再用凉水浸一天,小葱清炒,香滑爽脆,让人胃口大开。
而最让人惊喜的收获,是偶尔在茶树底下发现的几棵茶树菌,用来做汤,那种鲜香甜美的滋味是无与伦比的,我那是正长身体,一次只是用那个汤泡饭,吃下五碗!


种红薯
稻米之外,红薯是那时候最重要的作物,最多的时候,家里有一两亩面积六七处的旱土是种红薯的,早稻插秧下去后就开始“插茴砣”。
红薯是很容易种活的,翻过土,打出“洞子”,扦插上红薯苗,浇第一次农家肥,再敷一层土,隔几天也就成活了。不过中间也要管理一下,需要除一两次杂草;待到红薯藤快爬满的时候还要翻动一次藤子,因为红薯的茎会到处扎根长小红薯,若不翻动一下会导致主根处的红薯长不大。因父亲常不在家,一般锄草和翻藤的工作也是我做的比较多。
红薯的生长期比较长,一般到霜降前后才开始挖。红薯因品种不同而口味各异,最脆嫩多汁而清甜的是一种肉质红黄色的红薯,生熟都好吃;另外还有两种肉质淡黄和白色的红薯,由于含粉多,刚挖出时生吃硬而无味,但只要在薯洞子(贮存红薯的洞窖,一般开在黄土的山壁上)里存放一段时间,到快打霜的时候,这两种红薯的糖化程度就越来越高,吃起来甜脆爽口,甚至比之前那种红薯还要甜,有些红薯放到冬天里经常会有糖分从皮面上渗出来,这时口味是最好的。
才开始挖出的红薯,含粉多的那部分通常用来做红薯粉:在机器里打碎成浆放到大缸里,用纱布过滤,沉淀一段时间,倒掉上层的清水,底下就是洁白的红薯粉了,晾干后可以保存。
手工做红薯粉丝的话还有很复杂的程序,先要把干的红薯淀粉重新和水调湿,锅里大水烧开,在粉盘子(一种平底浅边的铁质圆盘)底抹上少许菜油,倒入调稀的红薯粉,漂在开水锅里烫至白浆颜色变透明,淀粉就结成薄薄的一层粉皮了,再从粉盘子中小心揭起晾到竹竿上,晾干至不粘手,取下切成细丝,再完全晾干,才可以收起保存。手工薯粉带有一种淡淡的天然香味,煮熟时软滑而劲韧,非常适口,且久煮不糊,既可单独做菜,也是煮火锅的极好材料,甚至直接在炭火上烤着吃,那也是很香的。
红薯的吃法有很多,生吃与打薯粉之外,那时也有煨在饭锅里吃的,很软而香甜;还有就是切片或者刨成丝晾干保存到冬天吃的;更精细点的吃法是放大锅里煮熟,加切碎的橘子皮等香料,用模型做成小薄片晾干,用菜油炸炒,就是一种很香脆的零食。
现在人吃红薯最多怕还是烤红薯,一般用碳火烤。那时我们也烤红薯,不过烤法不一样,一种是“煨烧茴砣”,即在灶膛烧过稻草后,将红薯埋在红热的稻草灰下面,空过个把钟头扒出来,剥开外皮,热气马上冒出来,跟着香味四溢...
另一种方法是我家独有,那时父亲是烧造青瓦的师傅,屋前就有一个瓦窑。青瓦也是普通柴草烧制的,到开窑的时候会从瓦窑顶部开一个小口释放窑内的余热,这时我们就用干净的铁丝串一串红薯挂在窑口烘烤,冬天的红薯,烤熟之后的表面都会流出糖分来,那种香甜软糯是很难形容的。


砍 柴
砍柴应该算是最古老原始的农村生产活动之一,历史悠久。不过现在农村大多也用煤气或用电做饭,一般都不担心燃料问题,所以极少再有人砍柴烧了。老家那些山林里的茅草和灌木都自由蓬勃的生长,无人伐刈,杂树茅草已经长到密不透风、无法容人。
但在我较小一点的时候,烧饭基本上还用柴禾生火。而稻草中的早稻草要做耕牛的越冬草料,并也似乎不是最理想的柴火,所以解决燃料,更多是到山里打柴,茅草和枯树杂木都比稻草好生火,火力足、灰分少。在那时每家都会分到面积不等的柴山,专供烧饭柴火之用,算是每家一种重要的私产。而每到秋天,上山砍柴就成了我们小姐弟三个的重要功课之一(家里有姐弟妹三个,妹很小就会做家务,六岁就开始下田帮做农活了)。
回想起来,砍柴也是很有乐趣的事情,用镰刀把大片的开始枯衰茅草和小灌木砍倒,在晴朗的秋天不几日就干透了,用草绳捆扎起来让父亲挑回家,在墙边上码叠成堆,一冬到春的燃料问题就解决了,能帮家里做些事,在我们小三姐弟是很有成就感的。而在砍柴的本身也不错:天气很凉爽,秋风吹憾着山林,落叶树上黄色、红色的树叶哗啦啦响,并有各种鸟雀不时惊起,鸣声悦耳,这就很让人愉快了。砍倒柴草时,草木本身的淡香味洋溢在空气里,很清新的气息。一般柴山上都有野果子树长着,有野柿子、结梨子等等,还有两种类似于橡子的野果(称之为lialia和kuku),以及一种小灌木上结的红黄色小果子,都不知道学名。可以吃,不过大人一般不让我们吃太多——就不吃,摘着玩也乐在其中。
砍过柴草的山林,显得空旷许多,在秋冬及初春的时节,这里就拓展成了小孩子们的乐园,爬树、藏猫猫这些原生态的游戏就在这里开展。但不要担心生态上有什么影响,柴草灌木每年都会长得很茂盛,客观上这种工作反而促进了山林生命的循环。而且有些冬春季节生长的野菜或药材都会趁机生长,夏枯草、淡竹叶等随处可见,背阴一些的地方生长有麦冬、矮茶(忘学名)、石蒜等,矮茶是治眼病的一种药材;而石蒜(现在好像叫彼岸花)是一种极漂亮的花卉,野生的也一样娇艳,颜色鲜红,花形也精致,幽幽的盛开在山林里,莫名有一种妖异的味道。


“搭虾子”
老家所处的位置半山半水,附近也有很多的水塘和沟渠,冬天里这些地方就是“搭虾子”的好地方。
其实家里的副业有不少,也有养过十多年的鱼塘,一般不愁吃鱼,不过在小时候的我们,捞虾是另有一番乐趣的事情。
那时我也会做捞虾的工具,从竹林砍两支斑竹(一种较楠竹细的竹子),一根火稍微烧一下弯成三角形做框架,另一支竹子做长柄,加一根短木棒扎成“T”字形,将三角形的框架固定在上面,再在三角形框架上绑一个尼纶细眼网兜,名为“虾舀子”的工具就做好了,还有一种工具叫“虾搭子”,做法有点不一样。
捞虾一般在冬天进行,打霜的早晨是最好的。外面有些冷得刺骨,但这并不影响捞虾人的热情,就捞虾而言反倒是越冷越好。这时虾米们都聚集在水沟或池塘旁边的水草从里,虾舀子小心的探到水下,从水草下往上兜,托出水面,无数长约半寸的小虾米就弹跳着滑向虾舀的底部,拢起来一次有半茶碗之多!而有几处沟渠的涵洞里的小虾更是密集,一次就能捞起一茶碗多的虾米来。后来有个人排干一个两米长的涵洞,居然捞到二十多斤小虾!我们每次早晨大约只捞半个小时,也会有四、五斤虾米的收获。捞虾时还会捞到一些小鱼,鳑鮍鲫鱼之类,有时也有较大的鱼进到虾舀里被捞上来,鲤鱼、财鱼、黄鸭叫之类,活蹦乱跳的,那就更让人兴奋了。
小虾米捞回来,母亲会把它们晒干贮藏,透明或青黑的虾子在太阳下慢慢变成红色,闻起来有种特别的鲜香,母亲把部分干虾卖掉,一部分自吃,虾子炒韭菜或者辣椒,还可以做汤,大约很多人都这样吃过,那种鲜美滋味就不多描述了;还有一种加工成虾酱的吃法,更加鲜香,但具体怎么做我有点不记得了。
那时年年捞虾,年年都会有不错的收获。但现在怕不能够,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老家的很多沟渠和池塘,那种小虾子已经极少见了。


其 它
打麻
苎麻是老家那时另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前一年把苎麻根切成一段一段埋到土里,开春长出来,到端午前后就可以“打麻”了。
之所以叫打麻,是先要用竹竿把苎麻的叶子打落,再把苎麻杆的皮剥下来。剥下来的苎麻扎成一束一束,放在水塘里浸泡几天时间,再用一种铁皮卷成的工具,从由苎麻的里面一侧刮过(苎麻的皮有两层,外层是粗皮不要,内层才是要的),外面的粗皮已浸得松脆了,自然就从内层韧皮上脱落下来,剩下细洁柔韧的内层部分。
把收获的这些苎麻晾干,也扎成一束一束的,有收苎麻的人来,就可以卖给他。那时奶奶在世,有时她也把苎麻纺成麻线,可以卖给打渔的人做渔网用。
挑猪食
养猪是家庭经济的重头,那时没有什么工业饲料,喂猪一般就是糠麸红薯及剩菜剩饭。也还不够,每天还需要到外面收集一些野菜,称之为“挑猪食”。这也是我们的“作业”之一,每天放学之后,姐弟三个各带一个篮子,田边地头四处“挑猪食”。
那时稻田里没有除草剂这种东西,因此在田埂上和稻田里都会生长一些野菜,有一种开黄色小花和一种白色小花的野菜是最常见的,只是都贴地生长,要从地上挑出来,所谓“挑猪菜”的“挑”字就很形象了。姐和妹都比我会做事,一般她们会先挑到满满一篮,多的又把我的篮子装满。
挑到的野菜都在池塘里洗净,装回篮子,但太沉,我们三个都提不动,转眼天快黑了,正自着急,暮色里却会突然看见父亲走过来的身影......
做 瓦
前面说过父亲原来是烧造青瓦的师傅,因此他那时手工做青瓦的情景我还记得,工序也比较复杂。
做青瓦的瓦泥,必须要用湖边的一种灰色粘土,因此先要从湖边把泥土挑到地坪里(一次要有十几吨)。瓦泥和湿,牛蒙上眼睛,牵到泥堆上,来回践踏,大概要持续半天,这时的泥才算是“熟”了。之后需要把做熟的瓦泥堆到一两米高,用铁丝切成规则长方体的泥垛。做完这些,父亲才能开始制作瓦坯:从泥垛上刨下长方形泥片有点像豆腐皮,包在一种圆筒状的木模上,再用“瓦荡子”(一种弧形木制工具)和另外一种切边的工具(不记得名字了,“钎子”?)配合,将泥片做成一个薄薄的圆筒,置坪里稍晾干,折拢就是四片瓦坯了。瓦坯不能晒太干,否则脆而易碎。制瓦坯的工作视天气而定,一般要持续半月到一月,制出的瓦胚总数约三万片时就可装窑了。瓦窑的修造也是复杂的工程,这里不赘述。瓦坯装窑后,一般大火连续烧两天一晚。然后是冷却,瓦窑顶上已预先做好一圈土沟,窑里停火后要挑水到窑顶,让水由窑顶和窑壁渗下,一般要十几担水。用水来还原瓦坯里的铁质,这才可以做出硬度够大的青色瓦片,否则瓦片呈红色而脆弱,不能用。完成这道工序后,瓦窑也稍冷却了,这才可以慢慢开窑出瓦。
父亲制瓦和烧窑的过程中,我一般会帮忙收泥坯,也会得到很多其它乐趣。做熟的瓦泥类似于现在的橡胶泥,正好可以用来做一些小玩意。这是我的拿手好戏,我用瓦泥做了好些东西:动物、人物和一些奇形怪状的器物,做好了也放到瓦窑里烧,那就可以保存很久了。不过烧出来的东西,只有一件比较笨拙的方形盒子保存较久,其它到后来都不见了,或者是其他人也看着喜欢带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