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总会有一些人,一些事会影响你的一生




公元2008年是一个注定会让人记住的年份,在这一年中国际金融的动荡给每一个参与投资理财的人带来的是经济上的损失,心理的煎熬;百年罕见的暴风雪肆虐,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在政府强有力的保障下得以消弥;5.12汶川大地震让每一位中国人为之落泪,每一个生命都牵扯着亿万人关注的目光;奥运会冲破重重阻挠,在这个己为太多的苦难所光顾的国土上举办,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成功了!......艰难困苦,挡不住一个民族前进的脚步,一次次挫折与磨砺,让中华民族精神得以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与一个国家的大事,与动荡的国际形势相比,个人、小家的痛苦与欢乐,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只是为了将来能有一个不能忘却的回忆,提起有些干涩的笔,记录下这一年发生在身边的事。“总会有一些人,一些事会影响到你的一生”,2008年,有近四分之一的时间与医院打着交道。




1、积患成疾




省城有一所著名的肿瘤医院,收治的病人多为来日无多的重症患者。许多站着走进来的患者,都是躺着出去的。怀一份侥幸,一份忐忑,存一份渺茫的希望,来到这个权威的医院接受最后的检查与治疗。得到医生的宣判后,心有不甘的病人和亲属们做着最后的努力:想方设法延长生命。于是,在连接医院那片新落成的闪着幽幽蓝光的高层住院部与那通向平凡人家生活的路北天桥,就成了一些所谓专家、秘方、包治百病、药到病除等小广告的衍生地。只要你从这座桥上走,那些散发广告的人就能准确的判断出是不是病人的家属,不失时机又极度热忱的塞给你一叠小广告。病急乱投医,许多不懂病理的人也会按图索骥,去找寻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也许是因为遗传因素,我们家的人很少生病,即使是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发病率也极低。家里常备的药只有去疼片和安痛定,身体不舒服,抠两片药扔到嘴里,算是解心疑,病也就慢慢的好了,打点滴是一种恐惧,也是一种奢侈。这也就养成了一个习惯:自我诊断与治疗,小病不说,大病忍着!




参加2008年春节晚会排练的时候,舞蹈队的姐妹们在一起聚餐,她们时常望着我苍白的面容发呆:“玲子,你怎么这样惨白?”我也感觉到最近两年越来越白,偶尔伸出手掌向着太阳望时,眼睛所能见的也是没有血色的苍白。“可能是在屋里呆得久了,不接受阳光晒,捂白了。”自我解释的这个理由根本经不起推敲,在座的每一位姐妹都娇生惯养,却都比我有血色。联想到这几年来身体的暗疾:每次那个的时候,大块大块的淤血和鲜红的血一同哗哗流下,弱小的我,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血可流?“可能是贫血吧”自己在心里小声嘀咕,却也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穷人家长大的孩子,有什么可矫情的呢。




只是,身体的不适很快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她们很快能够掌握的动作和技巧,我要慢慢的才能掌握。稍一劳累,便浑身浮肿。本来就上楼费劲的我要在一至五楼间歇一歇(一年前),现在要歇三次,才能爬上去,一进门就瘫坐在门口的沙发上,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平抑狂乱的心跳。之所以坚持,只是为了一份责任,为了不晾场,为了那些想看我舞蹈的亲人们,这个时候没有想到,已经病入膏肓。




积患成疾、病不藏形,从正月开始,就断断续续地高烧,因为无人体味身体的不适带来的心理上的折磨,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婚姻的不幸,已经使我伤痕累累,终于挺不下去,三、四月间数次昏厥。 讳疾忌医,对身体盲目的保守,终于积小患成大恙。市里的医疗技术不能最小程度的减免对身体带来的伤害,我和弟弟又辗转来到省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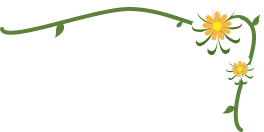


坐在医大二院的候诊区,等着弟弟在长长的队伍后面挂专家门诊。椅子冷冰冰,天气凉沁骨,心也似乎掉进了冰窟。一种茫然的绝望,在生老病死的关键时刻,我有谁可以依托?亲人们的宽慰已经阻止不了越来越近的病魔的脚步,泪水一串串的滚落,摔在冰凉的地面上,又溅开来,似无助的雨花。哀莫大过心死,对于上天慷慨借我的生命,还没活出精彩就要面对凋零残败的命运,太不公平。记起南唐后主的一首词: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宵汉,玉树琼花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樊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尤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我三十三岁的生命,在病中,在仓皇无助的日子中,有谁来对?




这个时候,前夫的电话号码在脑子里闪现,给他打个电话,看他对我是什么样的态度。于是,电话那头的他和我又拾回了一段柴米夫妻的情缘,一个在你病的时候,能够给你一份依靠的男人,还有什么不可原谅的?年少时的荒唐与孟浪,就各打五十,掀过那一页吧。




丈夫接到电话后,坐最早的一班车赶到省城,开始了我的救治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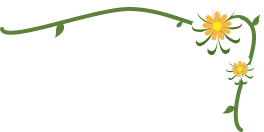


2、那时花开




在丈夫的安排下,入住肿瘤医院。开始了一系列繁琐的检查,只是在电视剧中见到的镜头就这样在我身边出现了:由浩浩荡荡的亲友团陪着(因为我是家里唯一一个得病,需要手术治疗的人,所以父亲、母亲、哥哥,弟弟全部上阵),在这个被我戏称为“鬼门关”的医院中,分工合作,有交款的、有购买入院用品的,有取送化验单的。在人情社会中,丈夫的社交能力发挥了作用,我可以不用排长队,就可以在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率先进入核磁共振的检验室,接受认真、细致的检查,部分费用也可以用合理的方式转移,让检查的医生满意,我也安心。医院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对医生的态度,人们可以量力而行。有的你给钱、她也不要,有的你不给、他也暗示你,有的他不收、你心里就如悬了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唯恐大夫不尽心。采取哪种方式,要相机行事,达到大家都满意。经过一至二十三楼的数次奔波,在手续完备,家属同意的条件下,主治的几名医生为我确定了治疗方案:保守治疗,采用微创技术去除肌瘤。




手术需要备血。采血的时候,看着冰冷的钢针刺入血管,那种“酥”一下的阵痛是我三十三年来很少体验到的,和以后十几天与针头的“亲密接触”相比,又是那样的微不足道。护士很奇怪,别人取血很顺利,我却没有多少血,需一次次的伸手握拳才能抽出供化验用的三管血。躺在病床上,等着挂术前必点的脂肪乳时,护士小姐冰冷着脸走了进来:你明天不做手术了。收走了术前所用的药品和物品,把我扔到了病床上。“怎么了?出什么意外了?”心中的一点狐疑很快扩大,变成一种沉入深渊的绝望:难道我得的也是不治之症?难道......恐惧一点一点地被放大,大到不可名状。




过了一会儿,两名主治医来到床前。“你看她白吧?那是重度贫血。”“那她嘴唇怎么这样红?”“那是爱美漂的唇。”主治的娄大夫翻开我的下眼睑,一片惨白,没有一丝血色。“你贫血都到这个程度了,怎么才来做手术?如果再来一次月经,流血就会流死,谁也救不了你了。”在他们的交谈中,我才知道不做手术的原因:血色素只有5.3克,常人的血色素值是12克,也就是说,我体内的血量不及常人的一半。这也就为持续了近两年的心悸、气喘、乏力,昏厥等现象的频发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这种情况,直接上手术台,打上麻药,你就永远也不会醒了!”“补血。400毫升一个单位的,先补三组,观察补后的血色素值再决定什么时候做手术”权威的主任下达命令后,一袋暗红、冰凉的液体一滴一滴的融入我的身体,那以后的岁月,我身体内三分之一的血液来自于三个今生也许都不会相遇的人,感谢他们,用无偿的付出挽回我这将颓的身躯。




经过三天的补血,血色素接近了手术所允许的安全值。终于,到了上台的时候,术前一天的准备让我肠胃皆空,行为乏力。换上病号服,扎上两个小辫,和亲人们进行简短的道别后,去三楼我与病灶分离的手术。爬上迎接我的滑动病床时,感到一阵透彻心肺的凉气,冷得浑身发抖。对未知手术的恐惧,犹如三九天掉冰窖--寒透了心。进入手术室,在宽阔的走廊候台时,左右各有两个病人。闲谈中才知道一个是脑瘤,一个是骨癌。看着他们恬淡的面容,听着他们舒缓的话语,身体渐渐的有了温度。和他们相比,我的这点小恙算什么呢?用丈夫的话来讲,上这个医院来治疗我这连“小感冒”都算不上的病,真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




先进的设备,高超的医术得以实施的一个前提:麻醉。麻醉师是几天前检查早已经熟识的张大夫,他和我仿龄,有一搭无一搭的和我说着话,以分散我对手术的恐惧。在大功率的手术灯照射下,突然存一丝盼望:快点做手术吧,把体内的这个定时炸弹早点摘除。“为什么还不给我打麻药?”“他们在开早会,稍等一会儿”小护士温婉体贴的为我整理好所带物品,埋上针,点上生理盐水。我知道,手术就要进行了。“下来吧,饭已OK,请来米西”张大夫通过对讲机与主治医取得联系后,拿起半针管的药走到我的身边,笑着将药注入点滴器,“猫有九条命,你这是第二条。”“你说谁是猫?”“她还知道我说她是猫”他和护士戏谑,我瞪着眼看他。“啪”一个面罩捂住了口鼻,人事不省的我进入了手术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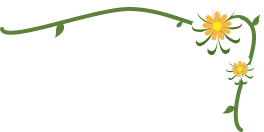


什么东西捆住了我?下意识的感觉到有人在身体上做着什么,却怎么也睁不开眼睛,手脚努力的挣扎,想要挣脱。恍惚中似乎听到有个男人骂了句什么,那个当初让我昏迷的面罩就又一次的扣在脸上,于是,还得睡去。“手术做完了,快醒醒”“醒醒”在许多人的呼唤下,在一阵朦胧之中,艰难的睁开双眼,看到身上的附属物由一个变成两个,左侧是个尿袋,右侧是个引流袋,暗红色的体内排出物似乎在告诉我,一个小患的正式终结。




麻药失去效力后,它的副作用也显现了出来。伤口的痛疼倒能用意志顽抗,不让焦虑的亲人担心。可术后的多痰却变成了一种折磨。因为伤口的牵引,体位的僵化,每一个稍大一点的动作,都成为一种煎熬。一次,父母近在咫尺也没能发现一口痰噎得要背过气的我,没能及时的为我翻身。于是,就盼丈夫来到身边,可那时,他因为劳累,正在路北的小旅店内蒙头大睡。




那以后的七天,先是在观察室内度过术后危险期,三天内的每天长达十七、八个小时的点滴折磨得人都要疯了。没有办法,在稍能下床走动时,就由身强力壮的丈夫高举重达7斤的“大白袋子”,拖着术后佝偻,羸弱的身躯在走廊内晃,那时艰难的每一步挪动,相对于在床上躺着不能动弹,又是一种幸福。




什么最值得期盼?那就是排气。一股气在腹内乱串。让你动弹不得,真应了一句俗语“肝肠寸断”。盼排气,怕排气,这个苦乐掺杂的过程,深深地印在人生的记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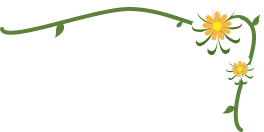


有享不了的福,没有遭不了的罪。在医院,这个社会的小舞台,心灵一次次的被什么东西触碰着,感动着。




3、别样亲情




进手术室的时候是七点半,出来的时候清晰的看到走廊电子表定格在11:06,观察室内,亲人们在等我,母亲最后一个由二表哥搀扶着走上八楼,“你知不知道,你这个小手术让妈多担心”、“十点半后,还不见你出来,我老姨的腿就软了。”望着母亲那为家操劳半生,为我担惊受怕的褐色、憔悴的脸,我侧过头,欲哭无泪。生儿养儿,不能借儿女的光,还要这样付出,母亲,你让我情何以堪!




本来以为七天就可以完成的治疗,因贫血的缘故,变成了十四天。下面,一些人物即将出场,她们是我的室友。每一个小家的不幸都折射着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亲情。




1床姐姐来自七台河,温婉贤淑,女儿在哈念大学,即将和男朋友奔赴辽宁某企业共创未来,姐夫(我们均叫做张大哥)在某局开车,家境殷实,见过世面,人憨厚质朴。2床是我同行,女儿相当出色,是北京科技大学的高材生,丈夫清秀俊朗,在某国企任中层领导,妇唱夫随,琴瑟相合。3床来自哈市郊区,她是唯一一个没有专人陪护的病人,四方脸庞,显示出一种特有的刚毅。脸色蜡黄,浓重的右眉角上有一颗很大的痣。在她术前,术中常来的一个人就是她二哥,照顾她,为她掏了手术的费用。看得出来,她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婚姻也不如意。就这样,加上我,我们四个女人和那些熙来攘往的亲友们在817病房内走过了半月的历程,我们由陌生走向熟识,留在彼此的记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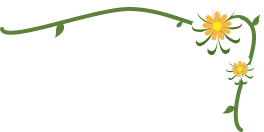


我入住的那天,一床姐姐刚从七台河转院过来,因为物品多,就随手放在了属于我的两个贮物柜内。近视的我在母亲的陪同下,昂首挺胸地来到病房,“一、二、三、......八,四个人,每人两个柜子,谁多占了?”我理直气壮地问,母亲则拎着住院的大包小裹小心翼翼地用眼神去探询,“吵什么!先放一下,这就让出来”那个小辣椒(1床大姐的女儿)嘴上也不让份,动作却很麻利,三下五除二的就把柜子让了出来。或许是病人特有的心焦,家属特有的担心,我和一床的友谊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了。人与人最远而又最近的是心与心的距离,走近的途径是用一颗包融博爱的心去体味。那以后,我们两家人的称谓似乎有点“乱”,我和丈夫叫他们夫妻为大哥、大姐,小辣椒和她男朋友管我叫“姐”,却称丈夫为“叔”,这可满足了我不大不小的虚荣心。大姐有着一双大大的眼睛,透露着无尽的安详,小嘴、柳眉,看得出来,年轻时一定相当漂亮,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她与大哥同学三年没有想到会结为连理,却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下成为夫妻,也算是天作姻缘。婚后琴瑟相合,走过了二十七个春秋。




肿瘤医院是个很人性化的医院,走廊的服务台上摆着每一个病人的病号卡,上面有的直接写着卵巢癌、宫颈癌,子宫肌瘤等病症,有的用字母代替,如宫颈CU、卵巢CU等曲笔,家属都明白,医生也明白,这是怕病人在走廊散步看到病情卡片后心理承受不了。所以,当家属决定保密时,所有的工作就必须仿照轻的手术病症的治疗方式走下去。




术后的第三天,刚能起身的大姐斜倚在病床上,拿着梳子为女儿梳头“姑娘,所有的罪都让娘遭了吧!只要你这辈子平平安安。”多么善良的母亲,大爱无言,为之感动落泪。想起刘和刚唱的歌中的一句话: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还没有做够,央求你啊下辈子还做我的母(父)亲,挚爱亲情,死生相依,在医院这个试金石的试验下,所能看到的都是大浪淘沙淘出的真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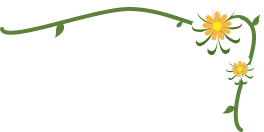


小辣椒的男友和朋友分别买花送给大姐。一个是盆栽的一红一绿两株苍劲的阔叶观赏植物,一个是束颜色各异的康乃馨。大姐没事的时候就浇浇水,闻闻花香




“你喜欢哪个?”她问




“我喜欢那个盆栽的,它让人们付出劳动,让人在对它的欣赏中体味存在的价值”,“而且,它虽然没有绚烂的颜色,馥郁的香气,却更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是啊,一个是一瞬的美丽,就走向枯萎。一个是平淡的真实,却长久的存在。”大姐边说,边开心地告诉我,那个盆栽的是姑爷送的,对女儿找对郎的喜悦溢于言表。我在心里默默祝福:好人一生平安。希望大姐能早日摆脱疾病的侵蚀,做一个健康的人,去安享儿孙绕膝的晚年。




从来没见过这样刚强的女人。因为有家族病史,3床在查出病变细胞介于正常细胞与原位癌之间时,果断地选择了妇件全部切除手术。在她脸上,看不到一丝悲悲切切,看不到一点点怨天尤人,在她二哥间或的照料下,她一个人坚持着。从术前、术中、到术后,从来没听她说过一句苦,一句难。偶尔她也拿我这个眼中的小妹妹打趣“啥事没有,一点也不痛,你可别有事没事就吓唬自己了!”因为她比我早5天做手术,她就用坚忍的微笑向我印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有她的存在,我们817病房的四大美女成了肿瘤医院一道靓丽的风景,每个人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乐观地对待病情,能够善以容人,达以兼物。就连就餐、就寝这样的小事也整齐划一,让其它病房的好生羡慕。




在她术后的第五天,传来了她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肺癌晚期,病入弥留之际的消息。老人家非常想见她,捎信让她回去。我们开了一个内部会议,大家一致不同意她回家,劝她过了七天危险期再走,只要再等两天。“不能等了,父亲没了,母亲一直由我照料,我如果不去,我老妈会担心,那样她就真活不了多久了,我必须得走。”看她默默的脱下病号服,换上常人的装束,在二哥的搀扶下走出病房,那一瞬,我看到她眼角的一滴泪。一个刚做完手术的人,硬挺着照料同在病中的母亲,是怎样的一种动力支撑她走下去?是亲情。金钱的多寡取代不了人间的挚爱,她并不富有,但却充实。她那薄情的丈夫在哪儿?她那没见过世面,在病房局促不安的儿子来过一次后,又去了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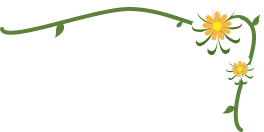


4、并不全是痛苦




这个结尾,搁置了两个月之久才动笔,那苦乐掺杂的人生历程中,总有一些快乐会让人记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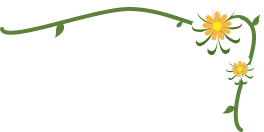


做完手术后,对食物的渴望相当迫切。医生在病人排气后,告诉可以喝一些汇源果汁。于是,家属们买来了许多:有桃汁,橙汁。一天,我们四个都在床上点滴,三床喝着橙汁,边喝边恍然大悟似地说:“我明白了,这个卖“登汁”的一定和医生有勾子,他收他好处费了,要不怎么只让喝“登汁”呢?一句话使我们笑得前仰后合,伤口的牵引却让这种笑变成了一种折磨。好不容易平息了笑,二床姐姐又说:“玲,我再说一句,你还得笑。”“哪句?”“登枝就上树了呗!”“求你别说了”大姐捂着肚子“再笑,我刀口就裂开了”。三床一脸不解的望着我们,非常疑惑:不就是“登汁”,为什么要上树呢?后来的几天,我有事没事就拿“登枝上树”来插科打混,她也不以为然。倒是丈夫,劝我不要再开玩笑,免得伤及别人的自尊,于是,及时收手。




新楼偶尔也会出现电路短路的状况,于是,病友们就准备了蜡烛来应付。三床走了以后,她的床铺就成了三个大男人的餐桌。照料我们吃完饭后,他们把各自准备的“大餐”摆上,那丰富的食物让几个病人垂涎欲滴,却因医嘱,而只能“望吃止馋”。三个男人推杯换盏,谈笑风声,烛光摇动,意切情真。在这个患难的小天地中,暂时放下心中的不快与苦闷,求得心灵的一次解脱。那些借着微弱的烛光在走廊内溜弯的病人与家属,常常被我们这种快乐所感染,投来一缕缕羡慕的目光。




闲也无聊,偶尔和丈夫讲点小笑话,猜点小谜语,既活跃了气氛,也有益于活络一下头脑。一天,出了这样一个谜面:没横没竖整十画,人人都有他。丈夫搔着不短的头发,左启发右提示,急得眼睛都憋成了一条缝,还是没能猜出来。“爹”我响脆地把答案说了出来,“哎”他答应的更利索。满病房的人都笑得要炸开了,我红着脸扫视了一周,还好,我爹不在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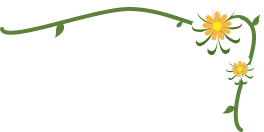


出院那天,三床的丈夫陪她一同来办出院手续,那个男人身材矮小,穿着一身蓝色的劣质西服,拿出本色行当,农村“司仪”惯有的油滑与病房内的每个人打着招呼。因为讨厌他对妻子的冷漠,我和丈夫有一搭无一搭的猜着谜。他走近我,搭讪:老妹,看你也是文化人,我出个谜,你猜猜。伸手不打笑脸人,心中再不屑,也得笑着面对。“鸿雁传书用嘴叼,一层更比一层高,凤凰山前双展翅,枕头褥子一起烧”,第一反应,这是一个猜人名的谜,到底是哪几个人呢?能想到的只有第四句的谜底:刘备(留被),他不失时机地加以点拨:传书,书是什么啊?古代叫“信”,“嘴叼”就是含着,合起来就是“含信”(韩信),有了这个提示,猜起来就相当容易了,三下五除二,有了正确的答案




鸿雁传书用嘴叼--韩信(含信)




一层更比一层高--罗成(摞成)




凤凰山前双展翅--岳飞(要飞)




枕头褥子一起烧--刘备(留被)




看着他那因我猜对而显得谦逊的脸,感觉也没有那样难以接受。只是,他为什么在该出现的时候不出现,让一个女人面对人生中这样一份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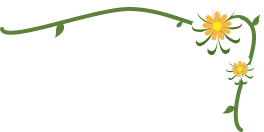


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宴席,在肿瘤医院、在817病房与每一位生命中注定要遇见的病友们在一起,承受着生命中不得不承受之重,又要面对分开的结局,只存一个想法:好人一生平安。走出这幢蓝色的大楼,希望------这辈子,不要再来!




“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经历过一场病痛,对许多人事看得不再那样执拗。人生就是一个旅途,此时花开、彼时花落,存一份豁达,一份超脱,才是真的来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