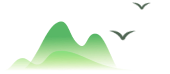沿着熟悉却又陌生的山路,我们走在回定西老家的路上。熟悉是因为这条路从小走惯了,而陌生源于方向不变,但却铺了水泥的路又宽又平缓,甚至有的小路已荒草杂生,无人问津,而是另开了水泥路。


车停在了二爸的场院中,我问弟弟迎面带着小孩的那人是谁。弟弟说:“那不就是丽丽吗?”我吃惊的打量着眼前的妇女:身材发福十分严重,与我记忆中的妹妹差了十万八千里,倒是皮肤一如既往的白,总之有七八年没见面了。记得在我上学时,她就外出打工,找了一个开饭馆的男朋友,家人不同意,于是偷偷跟人跑了。后来自然是带着孩子来认外家,不过好在丽丽过得好——定西有车有房,丈夫还在师专门口开着一个饭馆,算是嫁得好,不用在黄土地里刨吃食了。就连上学的我都后悔——上学有什么用?还不如找个好人嫁了!后来听家里人说丽丽离婚了,而且离得十分不光彩。男的回老家发展了,她净身出户,我却忘了问那三个小孩归谁了,眼前的这小孩是再婚后生的。


我们下了车,小卖部门口有几个人,我想一一打招呼,可是一时半会认不出谁是谁,想想大概有十多年没见面了,因此只是尴尬的笑笑,又回头看到大妈,二妈,三妈,姑姑等人,她们正忙着收拾饭菜,洗碗筷。吃一大碗家里的凉面,却再也尝不到小时候的味道,虽然回到了小村,但父母并不在身边的缘故吧!以前在她们跟前,我是小孩子,不必认真打招呼,不必认真周全的聊天,但现在是大人了,这个周全却不知如何开始。尕姐已经老的和几个妈都差不多了,我不知和她聊什么,是姐姐妹妹的天,还是对长辈的那种?在我的影响中,她家儿子也只有10岁左右,她也不过30岁吧,而我眼前的她似乎有了五十多:常年的田间劳作使她的脸紫黑紫黑的,脸上爬满了皱纹,牙齿外露的似乎更明显了,身体倒是十分结实,一看便知是劳动的好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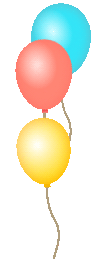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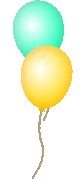
奶奶已80多岁,曾经光鲜亮丽的大厅房也尘土满地,房内空气也不十分流通,炕上也不干净,但我还是躺在炕上,像小时候那样和奶奶,姑姑说说笑笑。奶奶拉着我的手,眼泪溢满眼眶——多年未见是一层意思,再联想到爸爸的事,又加了一层。她老人家耳有点背了,但是看到我们小辈们在一起动嘴说话便又欣慰了许久。



我喜欢和姑姑聊天。我们和她在一起总是没大没小的,各种吐槽,她也不生气,总是乐呵呵的。我还喜欢她胖胖的身体,她个头不高,总给人憨憨的感觉。可能正因为她胖,总觉得她有使不完的力气——家里,地里都操持的井井有条,甚至年轻的时候回娘家也是背着各种好吃的翻山越岭的来,来了又帮着娘家干活,给奶奶洗衣服……但她不喜欢吃肉,却为什么这么胖呢?然而这次见到她,依然是褐色的脸,鬓间的白发似乎又添了不少,腿脚不怎么灵便了,昔日忙个不停的小胖子依然忙着给奶奶洗衣服,修剪指甲,只是多年的田间劳作似乎耗费了那一身肉肉,整个人瘦了很多。
我们习惯于把姑姑叫娘娘。本来控糖的我一口气吃了好几个娘娘带来的糖饼,因为娘娘的巧手,我们几个馋鬼是从小知道的,只要去她家或者她来我家,我们都是扯开肚皮吃她做的美食。 娘娘是个任劳任怨的农村妇女。年轻时被爷爷强迫嫁给比自己大十岁的姑父,生一儿一女,日子在田间日头中一日比一日过的有光景。我很少见她穿什么新衣服,虽然比爸爸小,但看着老多了。见人她总是乐呵呵的,应该是个很阳光却没心没肺的人。但她也和很多只有家里,地头的农村妇女一样:闲话实在是多!有时听着听着,我会笑着喷几句:“你要钱干嘛?”,“我看姑父人好得很!”,“你以后少说哥哥几句……”当然,她也没心没肺的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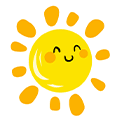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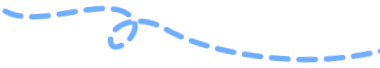

午后的阳光刺眼的射进屋内,空气更加沉闷了。我们拿着“老古董”小方凳,坐在树荫下吹着凉凉的风,不时聆听风抚过树叶的悦耳之声,享受风吹过脸庞的轻柔。再大口吃着西瓜拉着家常,真是“山中无岁月”啊!


小妹打来电话,说大家要去坟上了。
我们一行人到了二爸的坟地,开始把各种纸火从车上搬下来,放到坟前。几位爸爸们都坐在坟前;哥哥弟弟们准备烧纸,他们忙的忙着,不忙的跪在坟前;我们一帮女的跪在后面。这时我才发现她们头上都包着头巾,方便一会儿蒙着脸哭,而我和小妹戴着帽子。
突然,我前面跪着的尕姐哭喊了一声: “啊呀,我的爸爸呀,你孽障着,看看我呀……”着实让我不知如何是好!就在那一刻,似乎所有的女人都开始蒙着脸哭喊开了,唯有我和小妹低着头。此时眼泪也是大滴大滴的流着,但我实在哭不出声。看着前方大大的坟墓,我在心里问自己:二爸真的长眠于此吗?毕竟这是二爸的“百天”,毕竟二爸去世那天我未曾参与,毕竟我未亲眼看着他下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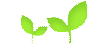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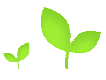
于是又想到与二爸有关的种种……
二爸似乎有鼻炎,说话时有很重的鼻音,并不时抽动鼻涕。有时他会突然到我家喝罐罐茶,其实我并不欢迎,因为我爸不喝,但我们要为了他准备东西,有时炉内刚加了一块碳,烟大得呛死人,但他依然要喝,好在他来的次数不多。现在想想,多希望那时他多来几次。
二爸家开着一间小卖部,爸爸妈妈总是使我去买这买那。我很少进他们家门,总是和着门口的狗吠声,尖声尖气的喊:“买货来,买货来……”有时喊一两嗓子,二爸或者二妈就出来了;有时喊破喉咙,他们就是听不见!然后我就扯着嗓子嗓子一直喊,喊到狗都不叫了,四下里都安静了,依然没人出来,我想他们不在家吧!有时二爸一出来就说:“这个女子,声音尖着,毛鬼丫头!”
有一次我们家要接秧歌,家里上上下下忙活起来。最让我看着震撼的是一大锅一大锅的面条,这么多饭,这么多人要吃!家里又使我去买东西,二爸问我家里做了什么饭,还剩多少,末了又说让我给他端一碗过来,我极不情愿的答应了。回到家,热闹的气氛一下子感染了我,二爸的话早被我抛到九霄云外了。第二日再见他,他半笑半责怪的说:“这个女子,小气得很!”
二爸是出了名的妻管严。二妈说的话他从不敢驳回,我想这也是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吧!多年来相安无事家庭和睦,让人看了也挺羡慕。只有有一年他俩干了一架,二爸好像打了二妈并离家出走,跑到永登爸爸的工地上打工,这事在我们村变成了茶余饭后的笑谈,都说二爸终于硬气了一回。后来二爸回来了,打工所挣的钱全数上交,二爸可真是好男人!
爸爸出了点事,去定西看望奶奶都是大晚上。那次刚到二爸的场院,我们准备悄悄去,冷不丁二爸用手电筒照过来,爸爸满是不自在却又不好表露。二爸后一步到奶奶家,我们都没怎么搭理他,倒不是因为讨厌,而是在爸那样的情况下,少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分心安。临走时,二爸低着头:“这条烟,你抽去!”他一边说一边把烟递给爸爸,爸爸也没多说什么,拿起烟,我们离开了。这可能就是兄弟情吧!
后来,我好几年没去定西了,即便去也是匆匆而已,很少见到其他人。去年听大哥说二爸住院了,我也是去会宁看完孩子,顺便去定西看望二爸。二爸躺在病床上,没有一丝血丝,脸和白发几乎同一种白,我抓住他的手,他喃喃地说:“花了不少钱了!”我只说二爸你好好养着,一定会好的。事后听家里人说是白血病,都瞒着二爸。年还未走远,二爸已离开人世,因婆婆住院,孩子住院,我未去奔丧。


看着眼前的坟墓,我仍无法相信,那里面躺着的是二爸。弟弟挑着燃烧的纸火,冒着浓浓的烟,在烟火的映照下,大大的门牙已不全了,三爸稀少的白发,大爸微驼的背……原来他们都老了,原来大大已经七十多了,但在我的回忆里,他们只不过50刚过。


“霞霞好几年没见了。”,“我们家……”,我听到身后蹲着的亲戚在谈论各种话题,因为他们是亲戚,不必跪着。我又将目光移到眼前跪着的女人们,姑姑和二姐还在哭喊着,只是声音弱了很多,几个儿媳妇低着头,但她们一律跪倒在地上,与其说跪,不如说瘫坐在地上,只有我和小妹腰板挺直的跪在玉米地里。后来哭喊声只剩低声呜咽了,我看着那堆燃烧的纸火,心里默念:要结束了!
我又望向那坟,我又在想:我为什么没有大声哭呢?是因为他只是二爸,而且是堂的,还是我本就感情淡薄?如果是爸爸或者妈妈,也许这会我已哭得不省人事了。呸呸呸,这只是想象,也只能是想象,我的至亲要长命百岁的。
坟前只剩灰烬和随风飘散的烟。弟弟说快起来,别哭了,我和小妹想拉尕姐起来,但她还是哭喊着,拉都拉不起来,同样娘娘也是别人拉也拉不起来。我们开始走了,浓浓的烟气随风跟着人群而来,似乎是二爸并不想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坟里,而是希望我们带他回家。


一条小路:
小时玩耍,上学,回家的小径已杂草丛生。
这条曾被村人们走来走去的路,我总站在院子里看来来往往的人。
有时一家人拉着架子车小心翼翼的从这条路穿行,生怕一不小心掉到我家院墙旁。
可是,只是,从什么时候小路如此狭窄了?
当下的我呀已活到记忆中爸妈的模样,
此刻的父母已老到脑海中爷奶的年岁,
眼前的奶奶已憨到想象中太辈的腐味,
碰到零零星星的老人们,我都认不出他们是谁们!
村子里的人真少!
想到李娟的文字那么静谧,那么纯真,又那么原始!
如果让我生活在这里,又将如何呢?
你是够安逸了,你是能田园了。
那么麻辣烫去哪里吃?美团又送到何处?充电宝去哪里扫?
……
所以,我只是我。
所以,我只能羡慕李娟!
所以,巴太或麦西拉只是传说!
……


一个人:
我们很少叫他姑舅爸,而是称呼他谢四。记得年轻时他总是放荡不羁,有很多女朋友,而且一个比一个漂亮,但最后都离他而去,要么给他留下一个儿子,要么女方带着女儿走了。妈妈总是提醒我,甚至生气的批评我,不许靠近他,在她眼里,他是个十足的“死狗”。记得当时我幼稚的独自发誓:如果我去定西上学学坏了,甚至跟着社会死狗混,我就去自杀!现在想想多可笑,我哪有混社会的资格呀!眼前的谢四已有了儿媳妇,看起来还是那么帅,却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身边自是有了新的老婆。


愿我的父辈们慢慢地老去,愿我的兄弟姐妹平安如意,愿我的小村永远岁月静好,四季皆安。我依然怀念树下乘凉吃西瓜的情景,闭眼静思时一股柔柔的风抚过脸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