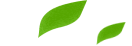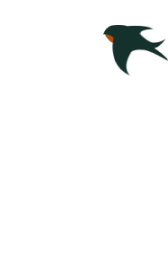写在前面的话:离家多年,记忆逐渐被岁月拿着橡皮擦,慢慢擦除。抱着“抢救文物”般的心态,记下这些文字,希望就此在记忆里画一个圈,避免岁月里的秘密花园全部流失,也许今天的记忆已有错乱或模糊,并不完全真实,那就且记且读吧。


距离上一篇纪事,不觉间已过一年。这回重新提笔,源自几天前午夜的一场梦。外婆家的老屋在梦里格外清晰,一帧一帧地像是放电影一般,哪个屋是怎样的格局,哪个屋住了谁,哪个位置摆着床……清清楚楚。梦里我向着谁一一介绍着,还反问她怎么不记得了。后来被膀胱叫醒,起床后我发现自己刚在梦里是错把现在的好友范老丝当成了一起长大的表姐海燕儿,故此絮絮叨叨地跟她说着老屋。等到重新上床入睡,又进去了这个梦,用梦中梦的形式又跟谁说,我刚梦到了外婆的老屋,还告诉她我错把范老丝当成了海燕儿跟她诉说老屋。
等到第二天早上醒来,想再回味一番老屋的样子,我才发觉它又变得有些模糊了,不似梦里那般清晰。掐指一算,老屋的这个布局,已然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如今老屋已经不在了,外公外婆,还有太外公的音容笑貌也已然模糊。这一场穿越回三十多年前的梦,大概是记忆在敲我的门,催我在更模糊之前记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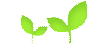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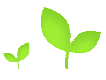
记忆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我会想不起昨天做了什么事,会忘记回复五分钟前的消息,但三十几年前外婆老屋的画面却在某一夜清晰入梦。更加离谱的是,我最早的童年记忆可以追溯到3岁。1985年,爸妈把我们家的老房子推倒,在原址改建两层楼房。因家里重造房子很忙,我就被送到外婆家住。因为住了好久好久,于是我吵着要回家,外婆抵不过我,只好送我回家。俩人走到家门口,我一眼看到自家房子没了,推倒的土屋像刚刚被耕过的田一样,大块大块的泥翻在地上,房子荡然无存,还有一帮人在上面忙活。我立刻大哭起来,说我家的房子呢?也许是这个画面对当时的我太过震撼,就在心里留下了烙印,近40年了,我居然还记得,是不是特别神奇?
外婆的老屋在记忆中最清晰的画面有两个,一个是厨房,一个是堂屋。厨房很大,除了墙角的土灶,还有屋子中间的四方八仙桌。记忆里的最温暖的画面是,哪怕没有大人同行,只有我们几个小孩在,外公外婆也会张罗一大桌子菜,盘子叠盘子的那种。但不论我们怎么叫,他们都坚决不上桌,笑眯眯地坐在边上看着我们吃,就觉得很幸福的样子。对于堂屋,我的记忆总是停留在冬天。大家围坐在堂屋的火膛周围,边上就是通往卧室和厨房的通道。大人们时不时往火膛里添两根干柴,又时不时把一块烧透的柴火夹进边上的坛子里,再加盖一块木板,土法制作木炭。我还记得那块盖坛子的木板上有着古老的雕花,长大后我不止一次地有点小遗憾,觉得那块木板要是收藏起来,搞不好是古董级别,现在早已不知所踪。火膛顶上的天花板挂着腊肉,火膛上方吊着铜水壶咕咚咕咚烧着开水,火膛里藏的是香喷喷的烤红薯、烤土豆、烤玉米,这热气腾腾的一幕,真如梦一般,透着烟火气、透着踏实感、透着幸福味。在这样的烟火气下成长起来的我们,总是有着柔韧的力量,也会叛逆,也会疲惫,也会emo,但总能站起来,这就是有人爱、能撒欢儿的童年赋予的力量。


老屋的门外,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池塘,放今天,老屋也可以算作“湖景房”吧。老屋的一侧,是一条铁道,我们去外婆家,在公路边下了车,还得走一段铁路才能到达。我也常常看着在屋边轰隆轰隆、呼啸而过的绿皮火车,想着车上都是什么人,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迈出老屋的门槛,穿过长条形的“稻场”,就是横卧在老屋外的池塘,以及池塘边的一排树。池塘边几步石阶下去,就是洗衣石板,外婆常常蹲在水边,在衣服上抹上肥皂,用棒槌砰砰地拍打衣服,再拿到水里荡一荡,再继续捶、继续荡。屋檐下的这一池水、这一排树、这一溜石阶,还有笑眯眯的老太太,以及回荡在耳边的棒槌声,就是一幅画,可惜我暂时还画不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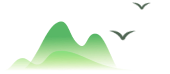
池塘边都种了什么树我已记不清,唯有一棵大大的老核桃树永远忘不掉。这棵树傍水而生,粗壮的树枝伸向水边。童年的我常常爬上去,坐在树上不肯下来。核桃树好上但却不好下,有一回我大概是爬的太高不敢下来了,最后是外公架着梯子把我救下来的。
青核桃这东西现在的小朋友怕是多没见过,硬壳外面包裹着一层厚厚的青皮,我小时候就常常坐在大树底下,用石头或者锤子敲烂青皮,再砸开硬壳,美美享用嫩甜的核桃肉。如果我们能穿越回去,看到的画面就是,一个瘦瘦的五六岁大的小姑娘坐在树下,双手和指甲缝都被核桃皮的汁儿染得漆黑,但她依然美滋滋地享用美食,并不在意美丑。
说起吃的,记忆之门就打开了,吃货的本质一览无余。除了有核桃吃,我还跟舅舅舅妈去山上采过鸡油菌,那菌子和腊肉炒起来,简直是香到了骨头缝里。再有就是铁路另一边,一个亲戚家种了一片荸荠,到了采收的季节,我们也去蹭点最新鲜的吃吃。印象中一锄头下去,一大块半干半湿的淤泥翻上来,里面就藏了好多荸荠,我们小孩子也会赤着脚下地,一脚下去,稀泥从指缝间冒上来,慢慢没过脚踝,用现在的话说叫“泥疗”,很治愈啊!放在今天,孩子们大概率会嫌脏,才不会下地,但其实那是最天然的,没有一点科技与狠活儿。


今天老屋已然不在,集中国传统女性特点于一身,善于隐忍的笑眯眯的外婆;精瘦慈爱话不多,因风湿而腿脚有些微行动不便的外公,还有那个90多岁除了有点耳背身体依然康健,爱在白米饭中加一勺白糖的太外公也都不在多年了。他们中最后一位过世,应该是在我读高三时,也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但依然还被记得。也许这就是人类与其他各个物种最不同,也最特别,最有价值的地方吧,也许这也正是文字存在的价值之一。
啰啰嗦嗦、心怀激动地写下这些文字,也算是为记忆延长了保质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