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红石头
芨芨草丛生
紧抓着沙砾的缝隙
夺命般地活着
有多少水,就有多少生命
在黑暗中挣扎
只为朝着阳光活着
让红石头变成连片的绿州
*注:红石头为地名
白 马
在巴润别立镇
一匹白马习惯了这里的冷
四只脚缓缓前行,始终让人无法想清楚
是左前脚还是右后脚先走
戈壁滩是北方的
沙漠是北方的
连这白马也是北方的
白马甩着马尾,我追随其后
在戈壁,我有一匹虚构之马相伴
再过长流水
水,绿了
从贺兰山顶,从戈壁深处
从额吉的脸膛流下
草,绿了
怀抱茫茫隔壁
从山脊上,从骆驼背上
在阿爸的眼窝上回旋
再过长流水
黄昏,有雨
替我滴滴答答滴绿了母亲的草原
注:长流水为地名


绿 洲
在江南说出绿的是北方人
在甘肃说出绿的是南方人
如果在腾格里沙漠说出绿,该是内心干渴的人
除了干渴,还拥有一颗蓬勃的心
装得下万物并能宽恕荒凉
用来自心脏的热血浇灌沙漠
用麦秆排成方阵
替我们拦住腾格里沙漠奔跑的野心
把水引过来,把根拴在沙漠里
围起篱笆,刀耕火种是不够的
还要向着上天,祈福生命的降临
用一颗卑微的小草的心
顽强地活下来
如果再说绿,就说生命之源
仰首阔步的沙,终抵不过一颗怀抱慈悲的心
黄 色
总有一些失重的颜色
比如我们看到黄沙的漫无边际
就不敢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看到腐尸,更想活上百年
怕干瘪的身躯被这黄色消耗殆尽
比起对生命的渴望,黄色
是楼兰的姑娘嘴角的笑
还是骆驼眼角的泪水
比起黄色
就想吮吸清晨沙葱叶尖上清澈的甘甜



苍天般的
第一次在英雄汇集的沙漠里
我看到统管英雄的苍天
沙漠是英雄的也是苍天的
快速爬行的黑甲虫是苍天的
每一个在沙漠的缝隙里挤出的生命都是苍天的
在这里,我要交出盘踞在身体里的欲望
装下苍天就够了
阿拉善博物馆
恐龙脚下洒落的汗水已凝结
和黄沙互相抚慰
它早已不再注意脚下的繁华
一个固定的动作矗立在正门口
人来人往
晚上还要继续睡进黄沙里
让自己越来越经风霜
眼神越来越空洞
但不管怎样,它都要学会不说话
默默地将故事变成坚硬的肋骨
支撑自己强大而似空无的内心


月光洒在贺兰山上
癸卯中秋的夜晚
贺兰山的月光追着万物
落雪般的
明长城上,墓碑旁的菊花上
奔跑的兔子身披铠甲
疾驰的列车反射白光
我们用心追赶着,借这一盏明灯
相聚。在瑶台镜下
共举可汗的金色酒樽
布布手印
那是谁的手,纤细修长
在生命最后一刻
试图在石头的藤蔓上抓住一根稻草
直到热血飞溅
在没有眼泪的石头上生存
除了流动的血
只有自己的硬骨头
瓷盘上的流水
水流沿着红泥白瓦
一路大珠小珠的滴落
像屋檐上的瓦当
盛上烟火和晃动的日子
深夜里碗与碟碰撞的声音
顺着光洁的边缘流淌
把清脆的,红润的颜色搅拌或叠加
从唇边划过的亲情,掂在掌心
时间的容器终究兜不住流水
这沙漠的驿站
东来西去的人在这里辗转北上
沙漠的盛宴
那些曾流过的汗,爬过的山
都将成生命里的徽章
悬挂在沙漠的胸前
后人重新退回戈壁
生起炉火吃大桌饭,跳集体舞
住橘红帐篷,而后匆忙在干渴中逃离
一段荒芜又一次开启
沙丘里数不清的长夜
被风举着旧账本
日日翻来覆去地清点家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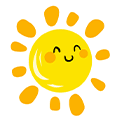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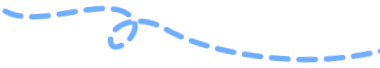

登贺兰山
在贺兰山的云杉林里
能依靠的只有石头堆里这一根枯木
能看见的只有两人
卷着军大衣,靠着牦牛塘的三层木塔
几万平方的草场和云山都是他们的
十月的风摇摆,没有方向
在草场上坐下来,一个人无需依靠
乌鸦飞不到的地方还有马铃声
鸟声。这是清晨的贺兰山
石头丛生,我突然心生欢愉
海拔两千七百多的地方
我要和石头一起
依靠贺兰山的风,活上百年
离别是一声叹息
弟弟送我们到车站,很近
故乡却还很远
戈壁看不见的边缘
矮树枝、梭梭草和双峰驼
经过亲人目送的路旁
挥挥手,一声叹息
路宽了又窄,公路和铁路反复切换
有多少人和我一样
父母站在异乡的站口
不得不北向亲人,越来越远
想起父母,沉默不语
车旁铁路的地基已建成
头顶安全帽的工人也许还有老乡
比起他们,我已怀抱富足
约定母亲下次坐火车前来
说起未来,一声汽笛
与王爷对话
一阵风沿着窄巷子
跟随身着九龙朝服的王爷入府
小莲在西厢房倚门垂首而立
方桌上备好茶点
我们坐在桌子两旁
说起隔墙的延福寺
王爷每夜入寝前
都耳闻转经筒上的铃声
门前的奇石馆
他经常徒步悠然穿过
每一个神态各异的石头都似众生相
读石偶然也会读到万物
后山上的敖包,他每年都按时祭拜
人与天相距良心
谈话之间鹿棋已成和局
像我们隔着时空与万物和解
2024年《草原》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