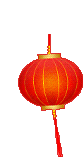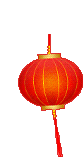
每一个走过生活的人,一定有TA自己的味道。像我的父亲留下的,是古早红糖的香味。
我很少吃成品的红糖,但很喜欢红糖花生馅儿的汤圆、青团,很喜欢红糖做的年糕,很喜欢守岁的鞭炮噼噼啪啪响过之后那一碗红糖白粿条。
暗红的温暖的,粗糙的方正的,红糖砖很喜庆地诱惑着我。年近了,红糖总要备起来的。为了方便随时取食,方方正正的红糖砖要敲一敲,随着红糖砖碎裂成无数小块,父亲的浓香四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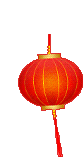
小的时候,家对面就是我们村里的红糖作坊。
冬至前,四里八乡的甘蔗收成了,青皮的红皮的甘蔗躺在板车里,躺在突突作响的拖拉机里被集中到糖厂的大院,煞是诱人。我总渴望父亲叔叔伯伯能豪横地拿起一根甘蔗,往膝盖上一磕,一节两节递到我手里。哪里需要什么削皮的程序,白生生的牙齿三下五除二便撕扯下脆生生的甘蔗皮,那甘甜的汁水胜过万千饮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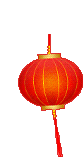
生啃甘蔗是幸福的,最幸福莫过于等待甘蔗汁煮成糖浆起锅的那一刻。记忆里冬至前后总是天寒地冻的,大人孩子们总爱往红糖厂挤,这里有大大的炉灶,五六口大铁锅一字排列,炉灶里的火红彤彤的,大铁锅上热气腾腾的,孩子们的脸蛋红通通的,空气里弥漫着甜甜的甘蔗味儿和孩子们躁动的心思。每一口铁锅前都有一位煮糖的青壮汉拿着长长的大勺子不停翻搅甘蔗水,甘蔗水逐渐熬成了褐红浓酽的糖浆时,家里有大人在煮糖的孩子们的高光时刻就到了。铁锅旁的空地上有两个大大的圆圆的竹匾,当一大勺一大勺的糖浆舀入竹匾时,早有大人将甘蔗削了皮,砍成一节节的拿在手上。糖浆入匾,他便姿态极好地顺势一扭,胖乎乎的甘蔗便裹上一层薄薄的糖浆。今儿煮糖汉子们的娃一个一个接过糖棒子,趁着糖浆还未凝固,一口咬下,那滋味儿神仙都不换吧?不曾吃上的孩子们哈喇子都流成串了吧?那时候他们都以自己的父亲为骄傲吧?我是尝过这样的滋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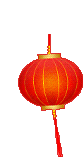
尝过这样神仙滋味儿的女娃儿极少,那年月的乡村重男轻女是默认的,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好吃好喝好玩大都紧着给男人男娃。父亲的世界里,我比男娃更受疼爱,好吃的好喝的我这个女儿一定第一份。我不知道我的弟弟是否尝过这样的滋味,还是像其他的娃们一样只能垂涎着竹匾中的糖浆凝固成糖,再被切成方方正正的红糖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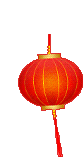
要过年了,老叔发来信息说大姑正月要过九十庆典,我敲着红糖砖又想起了我的父亲,空气里尽是父亲的味道。